约翰•卫斯理 Wesley, John

约翰•卫斯理 Wesley, John(1703~91)
生于英国北部林肯郡的厄普卫司,是撒母耳和苏撒拿卫斯理的第五个儿子。约翰与他的 弟弟查理斯(圣诗作者),是十八世纪福音复兴运动和循道运动的领袖。
卫斯理的家族有很深的宗教信念。他的祖父是清教的不从国教者;父亲受过高深教育,后来决定返回英国国教,并且在牛津大学受业;而约翰的母亲,不管是用哪一个世纪的标准衡量,都可说是个杰出的妇女。
约翰十岁即离家,往伦敦的查特豪斯受教育(1714),后来(1720)再在牛津的基督教会书院就读(学士,1724;硕士,1727)。他在1725年之前,没想过“要以宗教作为一生的事业”;这种改变可说是他的宗教或道德的改变,与十三年后的福音悔改同样真实、重要。同年,他受按立为执事,而翌年则成为林肯学院的院士。透过一个“宗教朋友”的影响,卫斯理开始阅读金碧士(参效法基督)、泰勒(1613~67,英神学家、主教,兼名作家和讲员,有“英讲坛之荣耀”之称),和劳威廉等人的作品。1727年夏,卫斯理离开牛津,在罗克特(Wroot)教堂担任父亲的助手,并且在1728年受按为长老。
1729年他在林肯学院的邀请下,返回牛津,很快就成了弟弟查理斯所召聚之群体的属灵领袖。其他学生称他们的团体为“圣社”,后来则改称为“循道派”,指他们凡事皆循规蹈矩,是语带讥讽的。无论如何,这群体一起研习新约希腊文,把无数的神学及属灵作品写成简易本,每星期禁食两次,每周领圣礼,并且定期探访病患的及坐监牢的人。
约翰和查理斯卫斯理于1735年父亲去世后,便离开了牛津,去美国乔治亚宣教。宣教期虽颇短暂,对兄弟俩的属灵生命倒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令他们改变的有两项因素,一是透过往美洲船上一班德国莫拉维弟兄敬虔的生活,另一是当时新兴的活动,就是以小组形式,给予完全奉献的男女信徒属灵训导。约翰于1738年回英国后不久,便遇上莫拉维会的牧师伯勒尔,他强调因信称义,内心有得救确据,及胜过一切罪恶。卫斯理深为这些信念折服,认为是与圣经、历史的基督教,及几个见证人的经验吻合,于是他也开始追求及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了。
1738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卫斯理参加了伦敦亚得门街莫拉维会的聚会,觉得心里“异样温暖”,皆因有人在会中宣读了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之序言。近代学者对卫斯理这个福音经验的性质有不同的意见,但后来的历史显出,这个经验实在影响了他每一方面。他由这经验而生出的热心,又联合了他弟弟查理斯和圣社其他会员(如怀特腓德),便形成了一股复兴的火焰,使伦敦、布里斯托尔,及报纸传媒触目。
强调个人藉信心而得救恩的经验,是当代英国国教之领袖视之为不需要的“新教义”,他们认为人单靠婴儿洗礼,就足以得救。很快地,大部分英国国教的教会大门都向卫斯理关闭,他们只得在街头聚会。1739年四月,怀特腓德邀请约翰去布里斯托尔,好把金斯伍德大批新信主的煤矿工人组织起来,以基督教教义牧养他们,训练他们成为门徒,这正是卫斯理最擅长的恩赐。
循道派神学的核心是爱∶神的爱是为万人的,而神的恩典亦是为所有人预备,只要人在耶稣基督内,以信心接受祂的救恩即可得到。
这种(预期的)恩典观所著重的乃是,神把自己给予每一个人,要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保障人真正有机会回应。称义或使人得救的信心,是恩典的结果;而悔改归正的经验,则是由两部分构成∶称义,那是基督的公义归到信徒身上;和新生或重生,那是圣灵把基督的义生在或归到信徒身上。成圣的恩典包括信徒由悔改到死亡之间,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卫斯理认为这工作既是即成的,也是渐进的。因为那是恩典的工作,是人只能透过信心来接受的,所以成圣可以是即成的。但“整个成圣”的工夫,基本上是人对神和对别人的爱,因此成圣就是神无限及大能的爱,在有限的信徒身上彰显的过程;就此意义而言,成圣就不可能是一种“绝对完全”那样的静态状况(这是卫斯理不断否定的),而是一种不断向前推进的状况。
约翰卫斯理的循道主义不仅是一套神学,而是一种对基督徒生活的了解,强调信徒与慈爱天父之间那种喜乐又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落实于人对上帝的敬拜,和对人的爱。爱失丧之人的意思,就是在传福音时“把基督给他们”;爱贫穷人的意思,就是社会关怀──为孤儿寡妇预备房子,提供免费医疗、食物、衣物、教育,及主日学等;爱初信者的意思,乃是训练他们成为门徒──小组牧养;倘若信徒给教区教会逐出来(当代英国国教对循道派信徒常采取的行动),便为他们举行圣餐;并且为初信者预备圣诗与属灵诗文、研经材料、祷文、单张、儿童祷文、日课、诗歌;出版成年人属灵的作品(包括神学和灵修的),每月的属灵杂志。总括来说,约翰有生之年一共写了四百多种不同的出版物。
在基督徒群体中,爱人的意思乃是诚实地放下偏见,同心协力,为要得着失丧之人(如∶“致天主教信徒的信”),加上真诚的合一(合一运动)精神,愿意从每一个真正属灵的传统去得着教益。他爱全世界的心,使他能说∶“世界就是我的教区”。他自己为宣教而去过的地方,包括乔治亚、德国、威尔斯、爱尔兰和苏格兰。自1769年起,卫斯理便差遣循道派的宣教士去北美洲,而在美国与英国战争后,更按立他们,使他们继续在前线工作。
卫斯理的工作实在惊人,在他五十二年的事奉生涯,平均每年走四千哩(骑马),共讲了四万篇道。但他最成功之处,乃是能选召、组织,及训练人成为属灵领袖,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透过不断成长的小组、地方领袖,和游行布道家,卫斯理能够维持宣教的热诚及其果子。他从不忽略对初信者的教导和训练,务要使他们成为门徒。从实际的意义而言,约翰卫斯理的循道主义,是牧养的更新,也是实践平信徒事奉工作的果子(包括男、女信徒在内),更是对福音神学和宣教的真实回应。透过卫斯理和循道主义,十八世纪英国广大的劳动阶层,终于有一种可行的灵修生活。
【见证】“给我一百个人,我就可以将英国翻转过来!”——约翰•卫斯理
——摘自《迥别的祝福》
若是论讲道,其实约翰·卫斯理讲得可能不如怀特菲尔德那样生动活泼。但是卫斯理极富组织及管理的能力,又博学多闻,对社会及国际局势深入了解。因此他不但成为整个福音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也成为针砭时代罪恶的先知。他的影响力,并不限于基督教的圈子内,更扩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所以,英国的福音大复兴运动,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响,约翰·卫斯理可以说是当居首功。
若要细数,约翰·卫斯理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实在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最重要的方面来略述一二:
1.循道运动(Methodist Movement)
其实约翰·卫斯理终其一生,都自视为英国国教的牧师,他也无意领导群众脱离英国国教。然而双方歧见越来越深,教会路线也越行越远。所以在约翰·卫斯理于1791年过世之后不到5 年,其追随者就正式成立了“循道会”。在中国,这个教会早期被称为“美以美会”,又有人称之为“卫理公会”。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就曾是美以美会最早按立的中国牧师之一。
历代著名的布道家很多,例如美国的慕迪(D.L. Moody)、葛培理(Billy Graham),中国的宋尚节,英国的怀特菲尔德等。但是约翰·卫斯理是与众不同的一位。因为大部分的布道家都只做劝人悔改、信耶稣的初步工作,但约翰·卫斯理却将这些刚信主的信徒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深入地、切实地做跟进和栽培的工作。这是他的独到之处。
卫斯理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却很实用,就是他组织了“班会”(Class) 和“会社”(Society) 。首先,他将十二人左右的初信者组成“班会”,并设立班长,负责监察及纪律的考核。每次班会的聚会,班长会轮流询问班员,是否有酗酒、赌博、打老婆等恶行。因为卫斯理深知,这些刚悔改的矿工和劳工,生活习性不是短时间可以改过来的。只有经由班长考核并推荐的人,才会准许受洗。这种模式是今天基督教某些“小组教会”的雏形,而约翰·卫斯理也应该被称为“小组教会模式”的祖师爷。
后来信徒日渐增加,从1742年开始,他打破传统,任命未被英国国教按立圣职的一般信徒为“平信徒传道”(Lay Preacher) ,后来又设立执事、教师及探访员等职,以分担牧养及关怀的工作。1744年开始,约翰·卫斯理又在全国设立几个教区(Circuit) ,每个教区由教区长(Superintendent) 负责管理,并由巡回传道人(Traveling Preacher) 负责教导与讲道。他又让妇女参与教会圣工,这在教会历史上是个创举,也是一大突破。
其次,约翰·卫斯理对教会模式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成立了“主日学”。但是当年这个所谓的“主日学”,与今天各教会流行的做法与目的并不相同。在当时,“主日学”乃是“在主日(周日)下午的文盲识字班”。而所用的教科书就是《圣经》,目的是要教导教会中占多数的文盲们读《圣经》。
其实这个构想最初并不是卫斯理或循道会信徒所发明的,而是由英国国教的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 首先提出的,但是在英国国教内他并没有得到响应,反而是约翰·卫斯理大力推动了这个计划。于是在十几年之内,全教会的信徒大部分都能识字了。到了信徒的第二代,很多甚至已经跻身于知识分子之列了。
虽然当约翰·卫斯理过世时,英国循道运动的信徒只有8万多人。但是他过世之后,循道会反而发展得更快。到了1850年,单单英国正式登记的会员就已经超过35万人。但是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是被低估的,实际上,应该高达200万左右,约相当于当时英国总人口的1/8 !
在美洲新大陆,循道会的发展甚至超越了英国,其中后来被按立为会督的亚斯伯利(FrancisAsbury ,又译为艾斯伯理,1745-1816)贡献最大。亚斯伯利未曾接受太多的正规教育,但是靠着自修,他后来甚至能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18岁就被按立为传道师,并在1771年自愿前往美国传道。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国教牧师和循道会( 当时尚未脱离英国国教) 传道师都逃回英国,亚斯伯利成为美洲大陆唯一的循道会传道师。
为了照顾在美国的信徒,1784年约翰·卫斯理就任命科克(Thomas Coke,又译为库克) 以及亚斯伯利为美国地区的共同监督 (Co-superintendent)。在亚斯伯利的殷勤传道下,美洲的信徒增加很快。从18世纪70年代的1,200 人增加到1813年的214,000人。亚斯伯利效法约翰·卫斯理的榜样,常常骑马巡回讲道,平均每年约6000英里,一生讲道超过16,000次,旅行达27万英里。
2.福音运动
然而约翰·卫斯理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他亲自领导的循道会而已。18~19世纪英美的整个福音运动,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如火如荼地发展着。甚至在英国国教圈子内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也是福音运动的结果。
虽然他自己被英国国教所排斥,循道运动也在他过世后五年,就脱离英国国教体系,成立了卫理宗的教会。而且在 18世纪末,英国国教内的神职人员中,可能只有不到5% 是福音派的。但是他在英国国教内部,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圣诗《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牧师,主日学运动的发起人罗伯特·雷克斯,国会议员威伯福斯及他的克拉朋联盟( 参阅本书第3 章) 等人,都是英国国教的牧师或信徒,却在卫斯理的感召下,推动或促成许多教会及社会的改革。
在英国国教之外,福音运动的影响力就更加明显了。有清教徒背景的“分离派”(Dissents,包括浸信会、贵格会、公理会等 )正式聚会的教堂,曾由1690年的251 处,降到1740年的27处,但是1800年又急速上升到926处。而非正式的聚会点(如家庭、谷仓等),也由1740年的506处,增加到1800年的3491处。可见福音运动使这些独立于英国国教之外的教会人数暴增。
不但如此,他们在教会和社会的影响力,更不是可以用人数来衡量的。因为这个福音运动不仅是宗教性的,更是社会性的。对卫斯理来说,社会改革乃是福音运动的“副产品”。因为福音的复兴,使基督徒个人及基督徒团体的良知被唤醒,更愿意委身于社会改革运动,朝向在世上建立公义的国度迈进。这在英国上层的政治家,以及基层的工人身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影响力。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德里(J. W.Derry) 在《19世纪英格兰史》一书中,从经济史的观点,评论这批因着福音运动而信主的政治家们说:“是这个福音大复兴,挽救了英国免于大革命。因着他们个人的信仰重生,改变了一个人,进而改变了周围的环境,终而改变整个国家。……这批循道会的政治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此外,历史学家汤普森在评论循道会的历史作用时,也认为福音派信仰一方面赋予工人以尊严,启发了他们的觉悟;另一方面,也教导工人遵守纪律,顺服权柄。因此,为即将到来的工业社会,培养出第一批敬业的劳动者。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名著《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这个结论。
3.社会改革
约翰·卫斯理看到社会实际的现况,陆续兴办了许多慈善事业。他所做的事既多且广,列举如下:
*在各地广设孤儿院及养老院,称为“陌生人友谊社”(Stranger’s Friend Society),以收容年老无依的寡妇及孤儿 ;
*设立平民诊疗所,提供免费义诊,以照顾工人及贫苦阶层。他甚至写了一本《基本的医疗》,教导民众简易的医疗和民间处方,再版达22次之多;
*创设“慈惠贷款基金”(BenevolentLoan Fund),规则是每人每次最多借20先令(后来增加至5英镑),然后在3个月内每周还钱,以帮助贫困者还债,免去牢狱之灾,并且贷款给小商人;
*设立习艺所,传授贫民谋生技能;
*设立京士屋(Kingswood)传道人子弟学校,提供免费的教育,后来更促成了政府举办国民义务教育;
*在教会内开设主日学,不但教导文盲识字,甚至开设简易的数学班,以教导家庭主妇记账,学习量入为出,以免负债。
此外,在约翰·卫斯理的感召下,还有许多人投身于监狱改革、贫民教育、医疗改革等慈善事工,而废奴及劳工法等种种社会改革法案,也陆续透过国会议员在推动。甚至在他过世后五十年之内,许多个人以及团体 (如救世军、青年会等),都还在继续推动社会改革的工作。
因此,卫斯理的福音运动,一方面教导工人们不要采取激烈的暴力对抗手段,要顺服执政掌权者,要成为“社会的凝结剂”。并且借着信仰,使劳工们的生活、品行都有明显的改善,也提升了他们的自尊、自信和自爱。同时,又发动国会议员、企业家及官员,进行由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使得社会改革的成果,透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程序,能够更加持久、坚固。在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英国成为第一个以法律保障劳工利益的国家,也是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国家。这种双向性的社会改革,是英国崛起的内在因素,也是福音运动所带来的成果。
约翰·卫斯理曾说过:“给我一百个人,他们除了神,什么都不爱;除了怕得罪神,什么都不怕。只要有这一百个人,我就可以将英国翻转过来!”因此,约翰·卫斯理所领导的福音运动,的的确确将英国翻了一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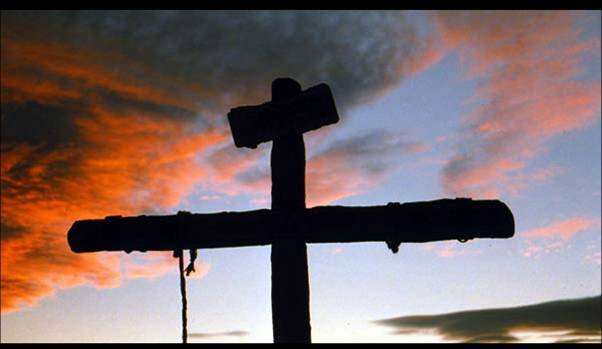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