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义思的故事 12 遭遇爱国主义情潮——《谁掌管明天》

欢迎收听宣教士的故事,我是晨风。今天我们要看的话题和爱国有关,爱国无疑是好事,一个不爱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人,怎么会为自己的国家祷告,又怎会愿意给同胞传福音呢,所以基督徒应该是爱国的,不仅爱国还要爱这个国家里每一个具体的人爱他们的灵魂。当然爱国也不能过头不能排外,更不能演变成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变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状态,这就不再是爱国的范畴了,往往步入了另一个极端。然而当年的何义思刚好便经历了这样的情形,当时发生了什么呢一起走进谁掌管明天的第九章遭遇爱国主义情潮。
一九二五年一月,冯晨星三姑和戚秀珍二姑从德国来到官山。她们正是理想中的传教士:愿意把自己完全献在祭坛上,尽忠事主,虽死不辞!两人加入我们官山这小小的传教士家庭,获得「家人」们热烈的欢迎。国籍的差异绝不会造成任何的隔阂——无论是德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都可以一同为神的国工作;宗派的分别也没有什么不便,路得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和长老会都能够携手同心,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拯救在罪里失丧的人!
春季的几个月里,官山、上海和圣巴巴拉之间,通信颇为频密。内地会驻中国的负责人焦牧师(Rev. G. wo Gibb)夫妇年前曾探访我们的父母,现在他邀请我往上海去参观内地会的总部。家里「差会的委员」也很赞成,这似乎是我暂别官山,出外走走的好机会。两位德国姊妹正在加紧学话,傅晨光姑娘已经可以处理一切文件书信,何姑娘管理小学和孤儿院,也弄得井井有条。五月初,我在十三天内旋风似的探访了全部十一间布道所,每天都马不停蹄地到处讲道。累吗?是的!但我倒以为是乐趣哩!
五月下旬,我便乘一艘德国轮船往上海,船上有其他要往内地会工作的德国姊妹,我们在一起深谈祷告,真有说不出的甜蜜!在上海,焦牧师夫妇热情款待我,使我感到十分愉快。不料,城里忽然掀起「排外」的暴动,一连数天,外国人在街上出现也不行,因为随时有杀身之祸。就我而言,这并没有多大不方便,反正我来上海主要目的是休息,不是观光。所以乐得躲在内地会的屋子里,睡个痛快!暴乱平静下来,我便冒险到船公司去,发觉有一班船期,刚好在我计划要离开的一天启航;我立刻订了票,也顾不得焦牧师他们恳切的挽留,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安排。
返抵香港,我才获悉全中国的工会已经号召一次「反英大罢工」,成千加中国人正离开这英属殖民地。我遇见几位朋友,刚提起我准备乘「夜船」去广州,他们急忙告诉我:
「要是你准备搭『夜船』,最好现在立即上船去!迟些便挤不上了……」
那时还未到中午,但我仍遵命赶到码头,发觉所有往广州的双层汽船(通常可载客一千名),似乎都已经客满了!走到最熟悉的「广东」号码头,那里也挤满了人,码头的大铁闸也锁上了。我呆在那儿好一会,不知道下一步应怎样行,只有默默求神指引。一位艇家走前来,问我是否想搭「广东」号,我回答说是,她便招呼我跟她走,说可以用舢舨载我到船的另一边,在那边上船。
「要是船上没有空位,那怎么办?」。我满怀忧疑的问。
「头等房一定有位!」
这乐观肯定的回答使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沿着岸边毕直的石阶下到小艇,再摇到船旁。我攀上底层甲板,拥挤的情形前所未见,连通往上层的宽楼梯也塞满了人。我提着衣箱,拿着纸包,再挟着雨伞,一面爬上梯级,一面口里要念着「对不起」,「借借光」等道歉的语句。尽管我竭力地东闪西躲,留意看衣箱不要撞到别人的膝头,或是纸包不要打着人家的脸庞,却发觉雨伞还是不受控制,已经刺着第三个人的肋旁!几番挣扎,好不容易才捱到梯顶。一个侍役看见我,便忙不迭地说客房已经全部租出。我告诉他不用房了,一张椅子也可以!
「那里恰好还剩下一张椅子。」
「好!我就要那张椅吧!」
我知道这是主特别为我留下的。那天,我坐在甲板上,耳边响起很多激烈反英的论调;幸好我可以读圣经和看书,不必整天听他门谈话。
第二天早上,到了广州。我看到街上满是人群;有工人、也有学生,举着反英口号的标语,到处游行示威。我在朋友处放下行李,便走到沙面见美国领事,希望顺便往银行兑现一张支票。那时还很早,银行仍未开门营业,我便在河畔树下的长凳坐了一会。静寂的河面,柔和的晨曦,与刚才闹哄哄的街道,正好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忽想然起诗篇的话:
「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那一天银行暂停营业,美国领事馆倒照常工作,但大使先生的态度非常严肃,我向他询问当时的局势,暴乱是否会蔓延到乡村如官山等地方?可是他只知道当天会发生一场大示威游行,于是极力劝我不要离开沙面,最好便在维多利亚旅馆避一避。我谢过他的意见,但没有肯定笞应他。
步出大使馆,我心中便不住向主呼求说:
「主啊!引导我前面的一步!」
还未走出外面的小径,我只觉得里面有一种力量在催迫着:
「回到官山去!」
从西桥离开沙面,步出了有英国兵守卫的铁闸,一辆人力车便走前来兜生意。但示威的人群中发出吆喝声,把车夫赶走。算了罢!我可以步行回去。我急步走过街中央,一路上避开人群。这时我才记起,刚才没兑到支票,现在口袋里不名一文。但我又想起钱包里有一张汇票,可以在广州邮政局兑现款。汇票是寄自星加坡由官山转到上海给我的。在中国这许多年间,这是唯一的一次用这种方法收到汇款。神知道我在广州那天需要一笔钱,便预早策划,让我得到供应。邮政局内一切宁静如常,街上示威者的狂热没有渗进这所建筑物之内。
我回到朋友那里,每个人都显得十分紧张,不知此次示威会不会弄出什么惨事来?很多人都劝我不要走动,但在我心里「回官山」的感动仍然十分强烈。我决定在中午渡河,在对岸的火车站趁下午一时半的火车回去。虽然离码头只有一条街之遥,但我行李很多,只得雇一辆人力车。旅店的老板放心不下,亲自陪我下到街上,直至我安全地登上车子。那时街道已经麇集了不少人群,车子就像在人海的狂涛中破浪而过一样。说也奇怪,车夫高喊「让路」的叫声,并没有引起任何对我这个外国人的注意,四方八面的人群却好像视若无睹……我买了船票,登上渡轮,不一会便到达宁静宽敞的火车站;刚才在街上饱受喧扰,至今才可以吁一口气。一个多小时后,我便在火车上,满怀高兴地直向官山驶去。
第二天下午,我才听见广州出事了:示威的队伍吵嚷了许久,终于组织成三哩长的行列,浩浩荡荡地沿著河岸前进,来到距沙面仅一哩的地方,中间相隔着一条狭小的水道,事实上示威的军人、学生和工人可算是守秩序了,他们只是间中喊几句口号、唱几首歌罢了;可是,英法大使馆的人员却为这对峙的局面感到焦灼万分。忽然,不知从那里传来第一声枪响,英国人想:「来了!」便立刻用机枪向游行队伍开火扫射,把他们一群一群地射倒。大抵他们忘记了那些只不过是无辜的学生;很自然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只有令中国人更痛恨那些丑恶卑鄙的白种人。为避免遭受报复,维多利亚旅馆的外国侨民都要立即撤离广州,登上一艘英国炮艇,狠狈逃生到香港去,直到几个月后事件平息了才可以回来。我没有听从领事的建议,真要感谢主!官山仍然一片平静,村民都认识我们,而且没有工会或学生组织的威胁,我们购买粮食也毫无困难。
渐渐,官山也被这股爱国热潮影响了。「爱国」,就是以「国家至上」为大前题;更憎恨多年来剥削中国资源的外国人!我们其中两位年轻的传道人,也因为热烈支持这个运动,被爱国的热潮冲昏了头脑。我们一切的劝告都无效,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外国人,不会明白他们中国人对国家热爱的程度!我们只好保持沉默,但在神面前却不住为他们祷告。
当我们正急需帮助之际,神差了一位中国牧师到我们中间来。这位区炽堂牧师已届中年,但目光锐利、谈吐爽直,曾经是毕牧师的同工,又数度来官山主持水礼,深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他抵达那天,有几位弟兄到码头去接他,然后一同回礼拜堂,特别举行了一个欢迎茶会。区牧师本来没有打算说什么,但禁不住大家盛意的请求,也就只好「说几句」了!
这「几句」一讲就是一个多钟头!在谈论中,他说出了我们外国传教士的心声;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了——神果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区牧师义正词严地表示,不论教会或基督徒个人,都只应让主耶稣居首位。其他的一切,包括国家民族,都在主面前成了次要。因为归根究底,能「救国」的,只有主耶稣,而并非高呼口号的示威群众。这次区牧师的访问,对我们官山所有的同工,尤其是差点误入歧途的弟兄,都有莫大的帮助和祝福。
此外,主又透过区牧师成就了另一件事——组织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一直以来,教会的行政都在外国传教士的手里,但现在中国信徒都有了强烈的爱国心,我们觉得转变的时机成熟了。在李星寿先生的帮助下,我们草拟了「教会中国化」的计划,现在再加上区牧师的睿智和领导,这些计划便更趋完善了。
第一次的教会代表会议终于在一九二六年初举行,由官山和各布道所的代表一同制定了会章,并立即实行。从此,教会将由中国人来管理和领导。至于我们外国传教士,除非被他们委任在各部门负责,否则无权过问。
新的制度并不表示教会内部产生了不协调的裂痕。一向传教士和中国信徒间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这个新改革是表明了更紧密的合作;为了基督的福音,大家愿意放下自己,溶合在主的爱里,成为一体!
都说民族主义一旦被煽动起来危害极大,而且难以浇灭。好在神一直在掌权,即便当时的爱国主义浪潮也影响到教会,但是神却借着区牧师的劝勉借着一系列的安排平息了这种盲目的情愫,而更多的激发起国人承担起真正爱国的行动,让他们更多委身教会事工承担起主所托付的使命,成为中国教会的主力。今天就为你播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你继续宣教士的故事,我是晨风,我们下期再见。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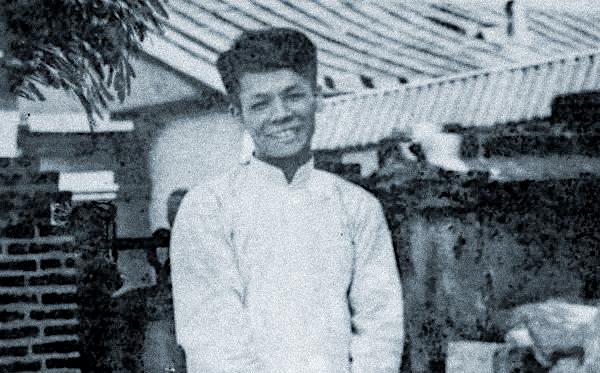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