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 第二十七集 第五章:作全群的监督(6):监督——忠心到底
亲爱的听友您好, 我是主播宣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香港灵石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来》。
†
五十年来 第二十七集 第五章:作全群的监督(6):监督——忠心到底
教团成立后,关于我们基督徒会堂的消息转趋沉寂。我那时不知道前途如何演变,只是每日都准备看遇见不幸的事。
我那时想到唐朝安禄山作乱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官吏都望风奔窜,河南北诸郡尽属于贼。
真源令张巡起兵于雍邱,后来睢阳被贼将尹子奇率大军围攻,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求救,张巡引兵三千进入睢阳,与许远一同守城还有张巡的部将南霄云、雷万春,都与张巡同心协力坚守睢阳,一直到城中食尽,将士病不能战,城陷被杀。
可是因着这几个将帅的忠勇,保全了江睢富庶之区。
我对我的几个同工讲论这几个人的故事,勉励他们作今日教会中的「睢阳勇士」。
我劝勉他们在这整个的教会都被撒但蹂躏的时期,无论如何总要为我们的主保守这一小块干净地土,纵使像张巡、南霄云、雷万春那样以身殉城,也不要向撒但屈服请降。
感谢神,这块干净土是保守住了,我们却未曾像那几位将帅以身殉城。
睢阳城终于失陷了,基督徒会堂却是屹立未动。这是神的保守、神的大能。
11月10日的午间,本段派出所警察送信来叫我即刻到日本宪兵队去。
我因为从日军占领北京后,日本宪兵队从来没有传过我一次,这次忽然传我到队揣想必是为教团的事。
我料想日方必是藉着宪兵队的威势劝诱我恐吓我,如果这次还不屈服,就先把我押下以后再对付我。我一点不会想到还有别的原因。
因此赶快拿了我的皮包装上我的圣经、眼镜盒、毛巾、牙刷和一双毛袜,又多穿了两件衣服,预备被他们扣下。
无论如何我仍是绝不参加教团。
我不但在神面前应许祂要顺服到底,我也在众圣徒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我有一日屈服,领我们的教会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你们就都即刻离弃我,再不要听我讲道,你们就称我为加略人犹大。」(这话是在10月25日下午5时圣徒聚会中说的。)
我已经破了釜,我已经沉了舟,我已经堵塞了我的退路。
那日我临出门的时候对妻说,「如果到日暮我还不回来,便是被宪兵队押下了。无论如何绝不屈服。」
我早就想到有一天宪兵队要拘捕我,我曾对我的几个同工们说,「如果我被宪兵队拘押,你们中间谁也不可为营救我而允诺参加教团。若是你们这样作了,我出来以后不但不感激你们,还要怪罪你们,并且我们还要自动的关门停工,因为我们已经失了节。」
那天我没有对妻多说什么话。她送我到门口的时候,我连头都没有回便走了。
到了宪兵队,看见有几个别的教会的「牧师」在那里,我讯问他们是为什么来的,才知道是宪兵队把他们传来办理移交英美差会房产的事。
后来向宪兵队的人问明,知道他们所找来的都是英美两国差会所设立的教会的牧师,并没有我的事,不过是因为派出所弄错了,才把我传去,我便回来了。
虽是一场虚惊,但回头一想,却是很有意味。感谢神,随时赐给我需用的力量,没有使祂的名受到羞辱。
从10月10日武田熙找我谈话以后,日方与教团方面都未再来找我。
起初几个月我还准备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及至1942年过去,我看再没有任何新的事态发生,才料想他们是不再过问我了。
1943年11月我到青岛去领会,听一位弟兄告诉我说,武田熙某次到青岛的时候,青岛教团分会的同人宴请他。
在席上有某君问他说「武田先生,华北各教会不是都必须加入基督教团吗?怎么王明道主持的教会不加入呢?」
武田熙回答他说,「我曾与王先生会谈过,他不加入的理由很充足,他的态度也异常坚决。我们无法勉强他们加入。」
某君再往下问说,「如果别的教会也像他们那样不加入,教团不是就散了吗?」
武田回答说,「别的教会也不能这样做。」
听见这番谈话,再证以1942年冬在北京间接听人传述武田先生所说与我谈话所得的印像,我明白那次他对我所表示的亲善不是恶意,乃是诚意。
感谢神,那天赐给我需用的勇气和信心,并在我身上成就了祂的应许「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十18-20)
神的话是那样真实可靠,投靠祂的人真是有福的。
†
今日回想那一场恶战因着神的保守得到了光荣的胜利,实在当欣幸感恩,可是在那时候却是十分的艰苦。
在日方军部的势力之下,谁敢略有反抗?还记得那时有一位朋友来劝我说,「明道,我劝你还是学聪明些。到不得已的时候再牺牲也值得,现在还不是牺牲的时候。」
我说,「这还不是牺牲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呢?」
他又对我说,「你不知道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个蚂蚁那样容易吗?」
我听他所说的这句话,当时心中确实有片刻的畏惧。
不久我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但我不是一个蚂蚁,我是至高神的仆人。神不许可,任何人不能加害于我。」
在那一年当中,信心有时坚固,也有时软弱。每逢听见一些险恶的风声,心中便涌起一片畏惧的波浪。
我自己生性就胆怯懦弱。父亲是在义.和.团.之.乱被围的时候因惧怕而自杀的。
我是他的儿子,我在这点上很像父亲。这次得着了光荣的胜利,是神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
我没有可夸的,我只夸神的作为、神的信实和神在信靠祂的人身上所显的大能、大力。
我的胆量虽小,我所事奉的神却大得无比。有些人说我大胆无惧,他们说得不对。
我一点不胆大,我更不是不惧怕。我惧怕得很。不过我怕得比一般人合适一些,我怕对了地方,我怕我得罪了神。
我确实的知道,如果我得罪了世上所有的人,他们都起来加害于我,只要神略一伸手,我便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但如果我得罪了神,以致祂向我发怒,降祸于我,纵使世上所有的人都想救我,也无济于事。
我不是不惧怕,我乃是怕那位当怕的神,却没有怕那些不当怕的人。
这场属灵的恶战最艰苦的一点,并不是他的险恶剧烈,乃是时间长久。
如果.战.争.的时间只有一天或几天,那就容易得多。纵使它只有一两个月也还好受。
可是它的时间自从一月延到年底。这样久的时间,每日在惊风骇浪中度生活。
准备着遭封闭,却未封闭;准备着被逮捕,却未逮捕;可是随时又有被封闭、遭逮捕的可能。
撒但在这悠久的时日中,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那种滋味、那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能明白。
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心思,人的感觉,人的爱好,人的畏惧。我愿意度着平安的日子,我惧怕身体的痛苦祸患,我知道日本宪兵队的残暴,我晓得囹圄中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我家中有年近八十高龄的老母,我不愿意她担惊受怕。
但为神的真理、神的荣耀、神的教会和我所事奉的主、所见证的道,我又不能向撒但高扯白旗,去作神的旨意并我的良心所不许可我作的事。
我感谢神,祂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祂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
我又感谢神,祂使我的同工和我的妻子都与我同心,没有一个人掣我的肘,他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回想1942年全年的岁月,无异乎在火窖中行走了三百几十日。
感谢神,在火窖中行走的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还有一位「相貌好像神子」的与我们一同行走,所以「火无力伤我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但以理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
自从经过了那一次的战争以后,我的信心和勇气都增加了不少。在那样危险的境地中,神都保守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一次宝贵的经验在近几年来使我得了不少的帮助。
从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中,我明白了牧养教会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许多信徒聚集在一处,各人的性情不同、知识不同、见解不同、背景不同,基督徒虽然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但各人还都有肉体和肉体里面的坏东西。
不遇见什么事或不长久相处,还不感到什么困难。一遇见事情或相处的日子一久,种种的纠纷便相继发生了。
有些人粗心大意,有些人精细谨慎;有些人心小量窄,有些人慷慨豪爽,有些人诡诈阴险,有些人正直忠诚;
有些人多猜多疑,有些人心地坦白;有些人视财如命,有些人挥金似土,有些人胆小如鼠,有些人勇猛似虎,有些人事事想从别人得利,有些人处处愿意帮助别人。
而且有长处的人也都有短处,总没有一个人只有长处,没有短处。把这许多人集合在一处,日久天长不发生摩擦冲突,真是不可能的事。
牧养教会的人需要照顾、领导这些人,也需要包容、疼爱这些人。
当他们彼此中间发生磨擦冲突的时候,需要为他们调解,稍不谨慎,便会把事看错,把话说错,以致使事态越发恶化。
就是说的话都十分公正、下的判断都十分确当,两方面因为都看见自己的理,却没有看见对方的理,便很容易认为他有所偏袒,因而对他发生误会。
牧养教会的人本是为爱主和爱群羊的缘故才肯费心、费力、费时光、费唇舌,去为他们调解。
谁想到竟因此招来误会,如果不存着慈母的心肠,谁愿意再过问他们的事呢?
还有许多时候存着爱心帮助人、栽培人、规劝人,那得帮助的人不但不知道感激报答,稍不如意竟会看那帮助他们的人为仇敌,给他许多打击和痛苦。
作父母的只有几个儿女,便常感受这种痛苦。一个牧养教会的人要照顾几十、几百个信徒,他所要遇见的打击和痛苦要有多少呢?
牧养教会的人还有一种困难,就是他们按着神使他们看见的真理,决定一件事情,进行一种工作,他们既知道那是合理的,当然要尽心竭力的去作。
有些信徒没有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便认为他们作的不对,其中有些人在他们的背后批评论断,也有些人在他们面前提出建议。
他们既清楚明白是应当作的,自然不能听了别人的建议便改变方针。这样一来,那些人便认为他们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于是便批评反对。
在这种情形之下,牧养教会的人要想向神尽忠,便不免遭一些信徒的反对;要想避免这种反对,就不能向神尽忠。
那些战兢恐惧、小心翼翼、时时看众人的面色行事、只求众人的欢心、根本不想到向神尽忠的传道人,自然遇不见这种难处,但他们也作不好神交托他们的事工。
我还记得1942年拒绝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那个时期,我们中间就有一部分信徒不赞同我的主张,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
他们认为参加那个组织既不是必须敬拜假神,又不是必须丢弃信仰,那有什么不可的呢?他们只看见工作,没有看见神向我们所要的忠贞和顺服。
那时有些人在我背后表示不满意,也有少数的人来劝我参加,我只有毅然决然的谢绝了这种建议。
当时确实有些人不对我表同情,认为我是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在一个长时期以后,他们才明白他们那时的见解是错误的。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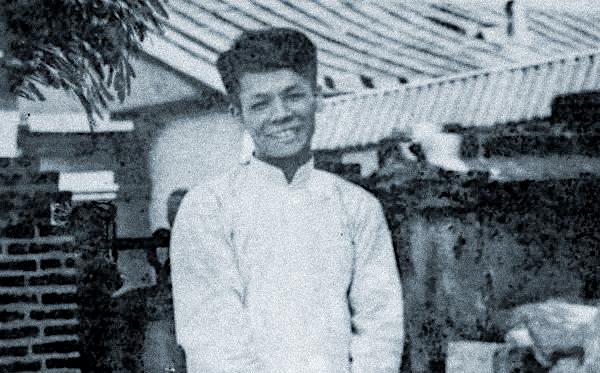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