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 第三十七集 :附录 追念母亲(1):恩逾慈母
亲爱的听友您好, 我是主播宣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香港灵石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来》。
†
五十年来 第三十七集 :附录 追念母亲(1):恩逾慈母
(这一篇中有几段记载因为在前几章中已经提过,所以删了去,免得重复;此外又增加了一些前次写的时候所遗漏的事情。)
1947年10月18日,夏令时间下午11时50分,母亲在北京甘雨胡同二十九号寓所平安去世。
自前一年9月1日姐姐因肠胃病去世以后,母亲心中就非常难过。
老年人丧子女本来就是最悲苦的事,若不是从神得着安慰,实在是极难担当,何况母女五十多年在一处就没有离开过呢?
加以姐姐病逝以前,母亲也同时患痢疾,姐姐一病不起,母亲渐渐痊愈,可是体健从那时一直就不能恢复,后来双腿都肿起来。
今年春夏比较还算好些,入秋以后,面部与双手也都浮肿起来。
请医生看过。说是年纪太高,身体虚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痛。
到入10月以后,身体更软弱,食量也减退。13日以后,情形一日不如一日。
15日情形更不佳。16日晚还能好好的吃一些食物,安静的睡眠一夜。
17日便不再想吃东西。晚间饮食都不能下咽。夜间有一位弟兄陪我坐在床前看守一夜。
昏睡中屡屡发呓语。18日除去进了几口饮料以外,已经不能吃东西。到了晚间,气力逐渐减消,脉搏也渐起变化,11时50分在毫无痛苦中安然去世。
按旧历计,82个生日过了两天;按阳历计,差4天不足82个生日。
母亲悟性不高,记忆力却相当的强,直到八十多岁,还能背诵幼年所念的四书、千家诗和一些别的古书里面的话。
母亲的性情憨直暴烈,领悟事理非常迟钝。
一件事情她认为怎样,便没有人能再为她更改过来,就是别人举出多少证据来证明她所看的不对,也难改变她的成见。母亲在老年的时候性情已经改变得很多。
在中年的时候非常暴烈,同人一交涉事情,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要生气。
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违逆母亲,母亲舍不得责打我,便自己生气摔毁东西,或是打自己。
同院邻不交涉事情则已,一交涉事情,十次中会有八九次要生气。
母亲同人交涉事情,不会慢慢的讲话,只会发急生气。
自己也知道这种性情,所以许多事总是忍受,不同人办交涉。
及至实在不得已去和人交涉的时候,很难得不把自己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姐姐和我在这一点上很像母亲。若不是神改变了我,我现在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步了。
母亲实在受过许多的苦。当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家中的生活非常艰难。每日吃很苦的饭食。
一到冬天,屋子既不够暖和,身上穿的衣服又单薄,母亲和我手脚总是冻得裂成许多破口,疼痛得很。
我年幼的时候常惹母亲生气,使母亲难过。不过却知道帮助母亲过日子。
没有力量作别的事,每天清早起来,便拿一个筐子,到本巷内几家大公馆门外倾倒秽土炉灰的地方拾些碎煤,拿回家里来生炉子,这样就减少家中一笔买煤的开支。
到我入校以后,仍是每天早晨拾过煤,再夹着书包去上学。一直到我十二岁住校,这件工作才算放下。
†
在我读书的时期中,走读的时候每月只交二三十个铜币的学费,还不算太难。
到十二岁住校的时候,连学费和膳费,每月要交二百几十枚铜元,(合银币两元几角),就感到困难了。
不过那时学校中有一种奖金,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第一二两名的学生,下一学期可以完全免交学膳费。
我在高小二年半之久,每学期总是因得奖金而省下了学膳费。那几年虽然不能再拾碎煤帮助家庭,但家中减少一个人的饭食,比拾碎煤节省了许多,母亲的日子过得稍宽裕些了。
到了我十四岁的秋季,从高小毕业,升入中学。(我从初小到中学毕业,都在伦敦会所设立的萃文学校读书。
那时学校改变了办法,增加学生的学膳费,招收外面的学生(以前是只收教友家的子弟)。
每月每个学生要交两圆钱学费,四圆钱膳费。但教会的学生可以由教会领到两圆钱的资助,每月自己付四圆钱。
奖金的办法也略有更改,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第一名的,第二学期免收膳费,考取第二名的,免收学费。
教会里学生的学费本是由教会担负,所以若考取第一名,免交膳费,那也就是不出钱读书、不出钱吃饭了。
到了我入中学二年级(我不太清楚记得是二年级或是三年级了)的时候,校中因为经费不足,把奖金缩减,改为高小一年至三年张贴总榜,中学四年也张贴总榜。
全高小、全中学各取两名,这四名学生可以得奖金。这样七个班次一共取四名,校中可以省下十名学生的奖金。
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时候,就靠着得奖金读书,母亲不过为我作衣服,给我一些买书和零用的钱。
到了我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奖金完全取消,只发一点奖品。
我最后所得的奖品是一本皮面金字的新约,和一本皮面带谱的颂主诗歌。
我在高小和中学的几年,既没有交过多少学膳费,家中的房租又渐渐增多,母亲受的苦当然也逐渐减少,这时比起十年前来,已经可算出幽谷而迁乔木了。
我作学生的时候,身体不好,常常生病。母亲为这个也受了不少的苦。
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母亲总是提心吊胆,只恐怕我的病不能好,有时深夜跪在炕前为我祷告,有时整夜不睡,看守着我。
我有几次耳内生疮,痛得我日夜喊叫。母亲为我用极热的毛巾放在耳朵上,昼夜服侍我,到我好起来为止。
母亲的爱多么浩大,多么真挚!我爱母亲还不及母亲爱我。
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巴不得再有几年的机会服侍母亲,但是母亲不在眼前了。
我希奇,世上会有许多子女把母亲看作讨厌物,看作分利者,看作累赘,看作仇敌。人没有良心竟能到这种地步,怎能不招来神的震怒呢!
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不明白母亲的爱,常常和母亲争吵冲突,使母亲痛苦,但母亲的爱总不因此减少。
当我在初小上学的时候,每日上下午从家中往学校去,母亲恐怕我在路上遇见什么危险,每次总要从家中把我送到学校。
我不愿意使同学看我那样懦弱无能,所以拦阻母亲,请她不要送我。母亲却坚持一定要送我。
我为这事屡次同母亲吵闹。母亲一方面恐怕不依从我使我不高兴,一方面仍是不放心让我自己走,所以便不再和我一同走,却在后面远远的跟着我。
有时被我发现,便同母亲吵闹,有一次我甚至自己咒诅自己。
我年幼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只住一间房子。我读了几年书,知道新鲜空气与人的健康大有关系,便提议夜间睡觉的时候多开窗子。
母亲却信一种旧说法,说夜间睡觉的时候应当把窗子关严,以免受夜寒、患重病。为这件事我也屡次同母亲争吵。
母亲既怕儿子受夜寒,又怕儿子心中不快活,便在我睡觉以前开着窗子,等我入睡以后,轻轻的再把窗子关严。
到次日早晨我发现窗子是关着的,便同母亲争吵。以后母亲便等我入睡以后把窗关严,早晨趁我未醒之前再把窗子打开。
有时清早我先醒了,发觉母亲又关了窗子,便又和母亲吵闹。
那时只知道母亲作得不对,却一点不了解母亲的爱,所以常常和母亲冲突。
如果在我尚未觉悟以前,母亲便离开世界,以后想起这些事来,却再没有机会对母亲尽一点孝道,那要悔恨到什么地步啊!
从我十四岁信主以后,我开始知道体恤母亲了。当我十七岁的春季,我们的学校从东城迁移到西城新校舍。
家和新校舍的距离与家和旧校舍的距离是十六比一。
从前是每星期六可以回家一次,迁移以后还是照旧,但心理上感觉着离母亲远了很多。
在校中的时候常常挂念母亲。先是挂念母亲的健康,后来渐渐转变,时常怕母亲死去。
我们的新校舍是一座四层的楼房,从楼上的窗子可以看见附近许多住户,也可以听见附近的各种声音。
那一带又多是贫民聚处,所以住户特别众多。每逢有人家死了人,便在门外挂一束白纸,找几个吹手,吹小喇叭、打大鼓。
我每次听见这种声音,便疑心母亲死了,心中苦痛得不能形容,恨不能立时回家去看一下。
盼到星期六中午,一下课就赶快回家。进了甘雨胡同西口,便胆战心惊,惟恐再看不见母亲。
及至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健康如常,这才放下了心。
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二三还要寄一封信回家,讯问母亲健好不健好。
从那时候起到母亲去世,母亲一直是我心中最挂念的人。
†
1921年的春季,我从保定被逐出校,回到家中,使母亲受了一次极重的打击。
有一天晚间我在我自己的小屋里听见母亲在对面的屋子里哭泣喊叫。
她说,「我要疯!我要疯!我再不能忍受了!」(北京人称患精神病为疯)。
我听见这几句话心中像刀刺一般。我怕母亲真要患精神病。
因为母亲有一次同邻舍争吵,神经失常,走到街上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才清醒过来。
我爱母亲。我不忍看见她那样受苦,更不忍看见她患精神病。我心中交战得十分猛烈。
我决定顺从母亲。我决定放弃神交托我的使命,好保全我的母亲,好救我的母亲脱离危险。
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主把一节圣经上的话放在我的心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十37-38)
这几句话在我的心中作了有能力的工作。我认为我应当爱我的母亲,但我更应当爱我的主。
我万不可因为体贴母亲便放弃了我的使命。不能,绝对不能!我只有把母亲交在神的手中。
纵使她因此患了精神病,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感谢神,祂真是信实的。那天祂试验我像古时试验亚伯拉罕一般。
亚伯拉罕为顺服神,舍了他的独生子,神却保全了以撒,使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那天我为顺服神,舍弃了我所爱的母亲,神也保全了她。那天母亲哭喊了一回,也就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她并没有因我的缘故患精神病。
当我在家中受神磨炼的那几年,我帮助母亲作家中一切劳苦的工作。
到1925年神交给我许多的工作的时候,祂照祂的应许藉着属祂的人供给我一切的需用,并使我能供养母亲,又为母亲雇了一个女仆,替我作家中的琐事,母亲的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了。
1925年的冬季,我在浙江省几处工作。那时因为战事,大江南北的铁路交通隔断了很长的时期。
从上海到北京的信件需要五六天之久。我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回家,但我很少收到家中的信。
母亲写字非常困难,姐姐又极不喜爱写信。有一次多日没有收到家中的信,我挂念母亲的健康。
恰巧有一次我梦见回到家中,看见屋内放着一具棺材,听说是母亲死了。
我难过到极点。醒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接连着好几次都在梦中看见不好的景象。
同时又多日得不着家中的信。我拍电报到家中,也得不着回电。
我更认为母亲一定是去了世,姐姐不肯告诉我。
那些日子我几乎患了精神病,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又拍一封电报给潘老太太。过了几天方得着姐姐的回电,报告家中平安,母亲健好这才放下了心。
†
母亲极疼爱我。一直到我四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常嘱咐我,像嘱咐小孩子一样。
每次我离京外出以前,必定嘱咐我不要到山颠水旁和其他危险的地方去,嘱咐我上下车船要小心,嘱咐我不要受寒,不要受热。
我为免去母亲挂心,出外时候最少每一周寄一封信回家。如果作长途旅行,在途中随走随往家中寄明信片,报告旅途平安。
如果出太远的门怕信件在途的日子太长,使母亲放心不下便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赶快拍电报回家。
最不幸的事就是从我结婚以后带了妻回家的那一天起,家庭中便发生了猜疑不安。
母亲和姐姐因为多年受苦的经验,使她们不能信任任何人,不能爱任何人。
母亲吃过姨母的苦,吃过邻舍的苦。从1925年家中雇了女仆以后,又吃女仆的苦。
我们所用过的女仆大多数都偷东西,就连浸在水中的大米,用水和成的面粉,她们都有方法偷出去。
二十几年的经验,使母亲认为除了她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要加害于她。
姐姐也认为除了母亲和弟弟以外,没有一个可爱的人。这种心理越来越深,家中的痛苦也就越来越重。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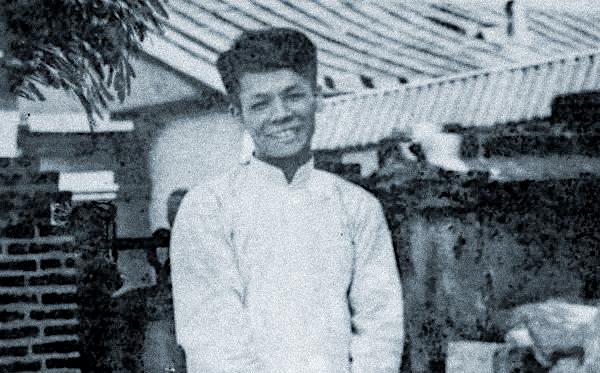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