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第四卷(上)

第四卷(上)
一
我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九年之久,陈溺于种种恶业之中,自惑惑人,自欺欺人,公开是教授所谓“自由学术”,暗中则使用虚伪的宗教幌子,前者是出于骄 傲,后者则由于迷信,而二者都是虚妄。
我一面追求群众的渺茫名誉,甚至剧场中的喝采,诗歌竞赛中柴草般的花冠、无聊的戏剧和猖狂的情欲,而另一面却企图澡雪这些污秽:我供应那些所谓“优秀分子”和“圣人们”[1]饮食,想从他们的肚子里泡制出天使和神道来解救我们。
我和那些受我欺骗或同我一起受人欺骗的朋友们从事于这种荒谬绝伦的勾当。
我的天主,那些尚未蒙受你的屈辱抑制而得救的骄傲者,任凭他们讪笑吧;我愿向你忏悔我的耻辱,为了你的光荣。
我求你,请容许我用现在的记忆回想我过去错误的曲折过程,向你献上“欢乐之祭”。
如果没有你,我为我自己只是一个 走向毁灭的向导!即使在我生活良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饮你的乳、吃你的不朽的食物的人!一个人,不论哪一个人,只要是人,能是什么?
任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嘲笑吧!我们,孱弱、贫困的我们,愿意向你忏悔。
二
在这些年代中,我教授着雄辩术,我身为私欲的败将,却在出卖教人取胜的争讼法术。
主啊!你是知道我希望教些好学生、当时所称的好学生;我一片好意地教他们骗人之道,不是要他们陷害无辜,但要他们有时去救坏蛋。
天主啊,你远远望见我在斜坡上摇摇欲坠,我在浓雾中射出一些善意的闪光,你看见我在教导那些爱好浮华、追求谎言的人时,虽则我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但还能表现出一些良知。
在这些年代中,我和一个女子同居着,我们两人不是经过当时所谓合法的婚姻而结合的,而是由于苦闷的热情,我忘却了理智而结识的。
但我仅有她一人, 我对她是始终如一,并无其他外遇。
在她身上,我亲自体验到为子嗣而黾勉同心的婚姻与肉欲冲动的结合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违反了双方的意愿而生育子女,但对所生的也不得不加以爱护。
我还记得一次参加诗剧比赛,一个巫师问我如赢得胜利,结他多少钱作为酬报,我是非常憎恨这种龌龊的邪术,我回答说,即使能赢得一只不朽的金冠,我也不愿为我的胜利而杀一只苍蝇,因为这巫师将杀牲祭祀魔鬼,认为如此则可以为我获致魔鬼的助力。
但是,我心灵的天主,我的所以拒绝,并非出于你所喜爱的真纯,因我当时只能想像物质的光华,还不知道爱你。
一个灵魂向往这种虚幻,不是“离弃你而犯奸淫”[2]吗?不是在信任谎言,“饲喂狂风”[3]吗?
因我虽不愿为我而举行淫祀,但我的迷信却天天在享祭魔鬼,魔鬼以我们的错误为乐趣,为嘲笑的目标,我们在饲喂魔鬼不就是在“饲喂狂风”吗?
三
为此,我是继续向当时名为算术家的星士请教,因为他们的推演星命似乎并不举行什么祭祀,也不作什么通神的祝告。
但是基督教真正的、合乎原则的虔诚必然加以排斥。
本来最好是向你、主忏悔说:“求你可怜我,治疗我的灵魂,因为我获罪于你”;[4]不应依恃你的慈爱而放肆,恰应牢记着你的话:“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才能避免遭遇更不幸的事。”
[5]这些星士们都竭力抹杀你的告诫,对我说:“你的犯罪是出于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金星、或土星、火星所主的。”
这不过为卸脱一团血肉、一个臭皮囊的人的罪责,而归罪于天地日月星辰的创造者与管理者。
这创造者与管理者不是你是谁呢?你是甘饴和正义的根源,你“将按照每人的行为施行赏罚”,“你绝不轻视忧伤痛恨的心”。
[6]当时有一位具有卓见之士,[7]并且也精于医道,在医学上负有盛名,他曾以总督的名义,不是以医生的名义,把竞赛优胜的花冠戴在我患病的头上。
这病症却是你诊疗的,因为“你拒绝骄傲者,而赐恩于谦卑的人”。
[8]况且,通过这位丈人,你何曾停止过对我的照顾,对我灵魂的治疗?
我和他比较亲厚之后,经常尽心听他说论。他的谈论不重形式,但思想敏锐, 既有风趣,又有内容。
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在研究星命的书籍,便以父执的态度谆谆告诫我,教我抛开这些书本,不要以精神耗于这种无益之事,应该用于有用的事物;他说他也研究过星命之学,而且年轻时,曾想以此为终生的职业。
他既然能读希波革拉第[9]的著作,当然也能理解这些书。他的所以捐弃此道而从事医道,是由于已经觑破星命术数的虚妄,像他这样严肃的人,不愿作骗人的生涯 。
他 又对我说:“你自可以教授雄辩术在社会上占一位置;你研究这种荒诞不经之说 ,并非为了生计,而且出于自由的爱好。
你应该相信我的话,因为我对这一门曾经刻苦钻研,已可以此为业。”我问他为什么许多预言真的会应验。
他照他的能力答 复我,认为这是散布在自然界的偶然的力量。
他说臂如翻阅某一诗人的诗集,一首诗的内容写的完全是另一件事,但可能有一句诗和某人的情境吻合,那末一人的灵魂凭着天赋的某种直觉,虽则莫名其妙,但偶然地、不经意地说了一些话,和询问者事实竟相符合,这也不足为奇。
这是你从他口中,或通过他给我的忠告,并且在我的记忆中划定了我此后研究学术的方向。
但在当时,这位长者,甚至和我最知己的内布利提乌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纯洁的青年,最反对占卜的——都不能说服我使我放弃此种术数。
对于我影响最深的,是这些书的作者的权威,我还没有找到我所要求的一种可靠的证据,能确无可疑地证明这些星命家的话。所以应验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出于推演星辰。
四
在这些年代中,我在本城开始我的教书生涯时,结识了一个非常知己的朋友,他和我一起研究学问,又同在旺盛的青年时代。
他本是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就学 、一起游戏的。
但幼时我们两人还没有深切的爱情,虽则后来也不能谓是真正的友谊,因为只有你把那些具有“因我们所领受的圣神而倾注于我们心中的爱”[10] 而依附你的人联结在一起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
但那时我和他的交谊真是无比甜蜜,同时,因嗜好相同,更增加了我们的投契。
我又使他放弃了他青年时代尚未真诚彻底认识的真正信仰,把他拖到了我母亲为我痛哭的荒诞危险的迷信之中。
他的思想已经和我一起走上了歧途,而我的心也已经不能没有他。
你是复仇的天主,同时也是慈爱的泉源,你紧紧追赶着逃避你的人,你用奇妙的方式使我们转向你;这温柔的友谊为我说来是超过我一生任何幸福,可是还不到一年,你便使他脱离了人世。
任何人,即使仅仅根据个人内心的经验,也不能缕述你的慈爱。
我的天主, 这时你做什么?你的判断真是多么深邃他患着高热,好久不省人事,躺在死亡的汗液中;
病势看来已经绝望,便有人结这个失去知觉的病人行了“洗礼”,我也并 不措意,认为他的灵魂一定保持着所得于我的思想,而不是得于别人在他失去知觉的肉体上的行动。
岂知远远出于我意料之外,病势转好,没有危险了当我能和他讲话时——只要他能说话,我即能和他谈话,因为我日夜不离,我们两人真是相依为命——我想把他在昏迷中领受“洗礼”一事向他打趣,以为他也将自哂这回事的。
岂知他已经知道自己受了洗礼。这时他惊怖地望着我,如对仇人一般, 用突然的、异乎寻常的坚决态度警告我,如果我愿意和他交朋友,不能再说这样的话。
我愕然失色,竭力压制我的情绪,让他保养精力,以为等他恢复健康之后, 我对他又能为所欲为了。但是他从我疯狂的计划中被抢走,保存在你的身边,作为我日后的安慰。
几天后,我又在他身边时,寒热重新发作,便溘然长逝了。
这时我的心被极大的痛苦所笼罩,成为一片黑暗!我眼中只看见死亡!本乡为我是一种刑罚,家庭是一片难言的凄凉。
过去我和他共有的一切,这时都变成一种可怕有痛苦。我的眼睛到处找他,但到处找不到他。
我憎恨一切,因为一切没有他;再也不能像他生前小别回来时,一切在对我说,“瞧,他回来了!”
我为 我自身成为一个不解之谜:我问我的灵魂,你为何如此悲伤,为何如此扰乱我? 我的灵魂不知道怎样答复我。
假如我对我的灵魂说:“把希望寄托于天主”,它不肯听我的话,这很对,因为我所丧失的好友比起我教它寄予希望的幻象是一个更真实、更好的人。
为我,只有眼泪是甜蜜的,眼泪替代了我心花怒放时的朋友。
五
主啊,这一切已经过去,时间已经减轻了我的伤痛。我能不能把心灵的耳朵靠近你的嘴,听听你给我解释为何眼泪为不幸的人是甜蜜的。
你虽则无所不在, 但是否把我们的苦难远远抛在一边?是否你悠悠自得,任凭我们受人生的簸弄?可是我们除了在你耳际哀号外,没有丝毫希望。
烦恼、呻吟、痛哭、叹息、怨恨能否在此生摘到甜蜜的果实?
是否因为我们希望你俯听垂怜,才感到甜蜜?对于祷告,的确如此,因为祷告时,抱着上达天听的愿望。
但因死别而伤心,而悲不自胜,是否也同样有此愿望?
我并不希望他死而复生,我的眼泪也并非要求他再来人世,我是仅仅因伤心而痛哭,因为我遭受不幸,丧失了我的快乐。
眼泪本是苦的。是否由于厌恶我过去所享受的事物,才感觉到眼泪的甜味?
六
我为何要说这些话?现在不是提问题的时候,而是向你忏悔的时候。那时我真不幸。
任何人,凡爱好死亡的事物的,都是不幸的:一旦丧失,便会心痛欲裂。
其实在丧失之前,痛苦早已存在,不过尚未感觉到而已。那时我的心境是如此。
我满腹辛酸而痛哭,我停息在痛苦之中。我虽则如此痛苦,但我爱我这不幸的生命,过于爱我的朋友。
因为我虽则希望改变我的生命,但我不愿丧失我的生命, 宁愿丧失朋友;我不知道我那时是否肯为了他而取法传说中的奥莱斯得斯和彼拉得斯,如果不是虚构的话,他们两人愿意同生同死,不能同生,则不如同死。
但当时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情绪:一面我极度厌倦生活,一面却害怕死。
我相信我当时越爱他,便越憎恨、越害怕死亡,死亡抢走了我的朋友,死亡犹如一个最残酷的敌人,既然吞噬了他,也能突然吞下全人类。我记得我当时的思想如此。
这是我的心,我的天主啊,我的内心是如此;请看我的记忆。
你是我的希望, 你清除了我情感的污秽,使我的眼睛转向你,你解除了绊住我双足的罗网。
那时 , 我奇怪别人为什么活着,既然我所爱的、好像不会死亡的好友已经死去;我更奇怪的是他既然死去,而我,另一个他,却还活着。
某一诗人论到自己的朋友时,说得很对,称朋友如“自己灵魂的一半”[11]。
我觉得我的灵魂和他的灵魂不过 是一个灵魂在两个躯体之中,因此,生命为我成为可怖的,因为我不愿一半活着 , 也可能我因此害怕死,害怕我所热爱的他整个死去。
七
唉,真是一种不懂以人道教人的疯狂!一个满腹委屈忍受人生的傻瓜!我当时确是如此。
因此,我愤愤不平,我叹息痛哭,我心烦虑乱,不得安宁,我一筹莫展。
我背负着一个破裂的、血淋淋的、不肯被我背负的灵魂,我也不知道把它安置在哪里。
无论在优美的树林中,在娱乐歌舞中,在清香四溢的田野中,在丰盛的筵宴中,在书籍诗文中,都得不到宁静。
一切,连光明也成为可憎的;一切, 除了呻吟和痛哭外,只要不是他,便使我难堪,讨厌;只有寄顿在呻吟和痛哭之中;但只要我的灵魂一离开呻吟和痛哭,那末痛苦的担子更觉重重压在我身上。
主啊,我知道只有你能减轻我的负担,能治疗我,但我既不愿,也不可能;我意想中的你并非什么稳定实在的东西,因为这不是你,而是空洞的幻影,我的错误即是我的天主。
我想把我的灵魂安置在那里,让它休息,它便堕入虚测之中 , 重又压在我身上;
我自身依旧是一个不幸的场所,既不能停留,又不能脱离,因为我的心怎能避开我的心,我怎能避开我自身?那里我能不追随我自身,但我逃出了我的故乡。
因为在过去不经常看见我朋友的地方,我的眼睛又会像在本乡一样找寻他。我离开了塔加斯特城,来到了迦太基。[12]
八
时间并不闲着,并非无所事事的悠然而逝:通过我们的感觉,时间在我们心中进行看令人惊奇的工作。
时间一天又一天的来来去去,在它来时去时,把新的希望、新的回忆注入我心中,逐渐恢复我旧时的寻欢作乐,迫使痛苦撤退;但替代的虽不是新的痛苦,却是造成新痛苦的因素。
何以这痛苦能轻易地深入我内心呢?原因是由于我爱上一个要死亡的人,好像他不会死亡一样,这是把我的灵魂洒在沙滩上。
这时最能恢复我的生气的,是其他朋友们给我的安慰,我和他们一起都爱着我当时所奉为真神的一连串神话和荒渺之言,我们这颗痒痒的心,用这些邪僻的东西来搔爬着,让它们腐蚀我们的心灵。
一个朋友能死去,神话却不会死。
此外, 在那些朋友身上还有更能吸引我的东西:大家谈论,嬉笑,彼此善意的亲昵,共同阅读有趣的书籍,彼此玩笑,彼此体贴,有时意见不合,却不会生出仇恨,正似人们对待自身一样;
而且偶然的意见不同,反能增加经常意见一致的韵味;我们个个是老师,也个个是学生;
有人缺席,便一心挂念着,而欢迎他的回来:所有以上种种,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形都出于心心相印,而流露于谈吐顾盼之间,流露于千万种亲厚挚热的情款;这一切正似熔炉的燃料,把许多人的心灵融而为一。
九
朋友之间彼此相爱便是如此,甚至可以到达这样的程度:如果对朋友不以爱还爱,会觉得良心的谴责;对朋友只要求善意的表示。
因此,一个朋友死去,便会伤心,蒙上痛苦的阴影,甜蜜变成辛酸,心灵完全沉浸在泪水中,死者的丧失生命,恍如生者的死亡。
谁爱你,在你之中爱朋女,为你而爱仇人,这样的人真是幸福!一人能在你身上泛爱众人,既然不会丧失你,也不会丧失所爱的人;
除了你、我们的天主, 创造天地并充塞天地,充塞天地而创造天地的天主外,能有不会丧失的东西吗?没有一人能丧失你,除非他离弃你,而离弃了你能走往哪里,能逃住哪里去呢?不过是离弃了慈祥的你,走向愤怒的你。
在你的惩罚的范围中那里能避得开你的法律?“你的法律即是真理”,而“真理即是你”。[13]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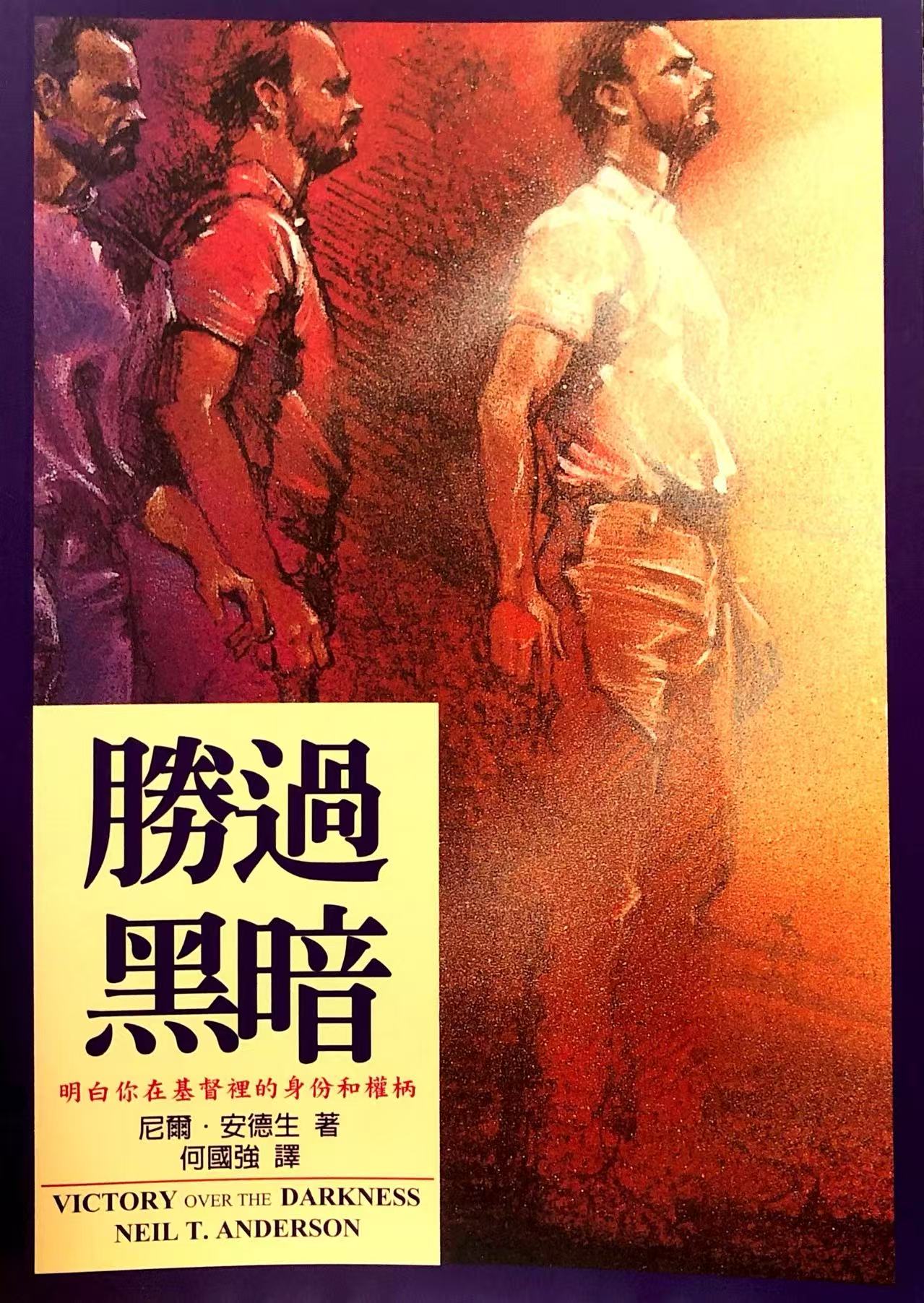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