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第四卷(下)

作者:奥古斯丁
第四卷(下)
十
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们转向你,请显示你的圣容,我们便能得救。
[14]一人的灵魂不论转向哪一面,除非投入你的怀抱,否则即使倾心于你以外和身外美丽的事物,也只能陷入痛苦之中,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如不来自你,便不存在。
它们有生有灭,由生而长,由长而灭,接着便趋向衰老而入于死亡;而且还有中途夭折的,但一切不免于死亡。
或者生后便欣欣向荣,滋长愈快,毁灭也愈迅速。 这是一切事物的规律。
因为你仅仅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部分,事物的此生彼灭, 此起彼仆,形成了整个宇宙。
譬如我们的谈话,也有同样的过程:一篇谈话是通过一连串的声音,如果一个声音完成任务后不让另一个声音起而代之,便不会有整篇谈话了。
天主,万有的创造者,使我的灵魂从这一切赞颂你,但不要让它通过肉体的官感而陷溺于对这些美好的爱恋之中。
这些事物弃向虚无,它们用传染性的欲望来撕裂我们的灵魂,因为灵魂愿意存在,欢喜安息于所爱的事物群中,可是在这些事物中,并无可以安息的地方,因为它们不停留,它们是在飞奔疾驰,谁能用肉体的感觉追赶得上?
即使是近在目前,谁又能抓住它们?肉体的感觉,正因为是肉体的感觉,所以非常迟钝,这是它的特性。
它所以造成的目的,是为了另一种事物,为这些事物已经绰有余裕;但对于从规定的开端直到规定的终点,飞驰而过的事物,感觉便无法挽留。
因为在你创造它们的“言语”之中,事物听到这样的决定:“由此起,于此止!”
十一
我的灵魂啊,不要移情于浮华,不要让你的耳朵为浮华的喧嚷所蒙蔽;你也倾听着。
天主的“道”[15]在向你呼喊,叫你回来,在他那里才是永无纷扰的安乐宫,那里谁不自动抛弃爱,爱决不会遭到遗弃。
瞧,事物在川流不息地此去彼来,为了使各部分能形成一个整体,不管整体是若何微小。
天主之“道”在 说:“我能离此而他去吗?”我的灵魂,至少你对欺骗也已感到厌倦了,你应该定居在那里,把你所得自他的托付给他;
把得自真理的一切,托付于真理,你便不会有所丧失;你的腐朽能重新繁荣,你的疾病会获得痊愈,你的败坏的部分,会得到改造、刷新,会和你紧密团结,不会再拖你堕落,将和你一起坚定不移地站在永恒不变的天主身边。
你为何脱离了正路而跟随你的肉体?你应改变方向,使肉体跟随你。
你通过肉体而感觉的一切,不过是部分,而部分所组成的整体,你看不到,你所欢喜的也就是这些部分。
如果你肉体的官感能包罗全体,如果不是由于你所受的惩罚, 官感不限制于局部,那么你一定希望目前的一切都过去,以便能欣赏全体。
譬如我们说的话,你是通过肉体的器官听到的,你一定不愿每一字停留着,相反,你愿意声音此去彼来,这样才能听到整篇谈话。
同样,构成一个整体的各部分并不同时存在,如果能感觉到整体,那么整体比部分更能吸引人。
但万有的创造者当然更加优于这一切。
他就是我们的天主,他不会过去,因为没有承替他的东西。
十二
如果你欢喜肉体,你该因肉体而赞颂天主,把你的爱上升到肉体的创造者,不要因欢喜肉体而失欢于天主。
如果你欢喜灵魂,你应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因为灵魂也变易不定,唯有固着于天主之中,才能安稳,否则将走向毁灭。
因此你该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尽量采取灵魂,拉它们和你一起归向天主;你该对它们说: “爱天主,是天主创造了一切,天主并不遥远。
天主并非创造万物后便功成身退; 万有来自天主,就存在于天主之中。
哪里闻到真理的气息,天主就在哪里。天主在人心曲中,而心却远远离开天主。
“叛逆的人,回心转意吧!”[16]依附于创造你们的天主。和他一起,你们便能站住,获得安宁。
为何你们要走上崎岖的道路? 你们要上哪里去呢?你们所爱的美好都来自他,但惟有归向他,才是美好甘饴, 否则即变成苦涩。
这是理所必然的,因为美好既来自天主,如放弃天主而爱上这些美好,当然是不合理的。
为何你们始终奔逐于艰苦的途径?你们想在哪里找到憩息之处,哪里也找不到。
你们找寻吧;决不在你们找寻的地方。
你们在死亡的区域中找寻幸福的生命,幸福的生命并不在那里。那里连生命都没有,怎能有幸福的生命呢?
他,[17]我们的生命,却惠然下降,他负担了我们的死亡,用他充沛的生命消毁了死亡,用雷霆般的声音呼喊我们回到他身边,到他神秘的圣殿中,他本从此出发来到人间,最先降到童女的怀中,和人性、和具有死亡性的人身结合,使吾人不再永处于死亡之中,“他如新郎一般,走出洞房,又如壮士欣然奔向前程”。
[18]他毫不趑趄地奔走着,用言语、行动、生活、死亡、入地、上天,呼唤我们回返到他身边。
他在我们眼前隐去,为了使我们退回到自己内心,能在本心找到他。他不愿和我们长期在一起,但并不抛开我们。
他返回到他寸步不离的地方, 因为“世界是凭借他而造成的,他本在世界上,他又现身于这世界上为了拯救罪人”。
[19]我的灵魂得罪他,向他忏悔,他便治疗我的灵魂。
“人的子孙们,你们 的心顾虑重重到何时为止?”[20]生命降到我们中间,你们还不愿上升而生活吗? 但上升到哪里呢?你们不是已高高在上吗?
“你们的口不是在侮辱上天吗?”[21] 要上升,要上升到天主面前,你们先该下降,因为你们为了反抗天主而上升,才堕落下来的。
我的灵魂啊,把这些话告诉它们,使它们在“涕泣之谷”中痛哭,带领它们到天主跟前,如果你本着热烈的爱火而说话,那末你的话是天主“圣神”启发你的。
十三
这一切,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所爱的只是低级的美,我走向深渊,我对朋友们说:“除了美,我们能爱什么?什么东西是美?美究竟是什么?什么会吸引我们使我们对爱好的东西依依不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美丽动人之处,便绝不会吸引我 们。”
我观察到一种是事物本身和谐的美,另一种是配合其他事物的适宜,犹如物体的部分适合于整体,或如鞋子的适合于双足。
这些见解在我思想中,在我心坎酝酿着,我便写了《论美与适宜》一书,大概有两三卷;天主啊,你完全清楚, 我已记不起来了。我手中已没有这书,我也不知道怎样亡失的。
十四
主、我的天主,我为何要把这本书献给罗马的演说家希埃利乌斯?
我和他并不相识,他的学识在当时极负盛名,因此对他崇拜;
我听到他的一些言论,使我很佩服,但主要还是由于各方面对他的褒扬标榜,我钦佩他本是叙利亚人,先精通希腊的雄辩术,以后对拉丁文又有惊人的造诣,同时对于有关哲学的各种问题也有渊博的知识。
人们赞扬他,虽则不见其人,而对他表示敬爱。这种敬爱之忱是否从赞扬者传入听者之心?不然,这是一人的热情燃烧了另一人的热情。
听到别人赞扬一人,因为相信是真心的赞扬,自然会对那人产生敬爱之忱,换言之, 对一人的赞扬是出于内心的情感。
为此,我是依据人们的判断而爱重一人,不是依照你天主的判断,但惟有你不会欺骗任何人。
但为何人们的赞扬希埃利乌斯和赞赏一个赛车的有名御者,或群众所称道的猎手大不相同,而是怀着尊敬的心意,一如我也希望受到同样的赞扬?
为何我虽则赞赏、崇拜舞台上的脚色,却不愿别人赞我、爱我像伶人一样?
我宁愿没没无闻,却不愿得到这种名誉,我宁愿别人恨我,不愿别人这样崇拜我。
在同一的灵魂,怎会分列着轻重不等各式各样的爱好呢?为何我欢喜别人身上的某种优长, 而在自己身上,即使不深恶痛绝,至少表示讨厌而不肯接受?
我们不都是人吗? 一个爱良马的人,即使可能变成马,也决不愿自己变成马。
可是对于优伶不能如此说,因为优伶和我同属人类。
然而我所不愿的,却欢喜别人如此,虽则我也是人。
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主啊,你知道一人有多少头发,没有你的许可,一根也不会少;可是计算头发,比起计算人心的情感活动还是容易!
至于那位演说家是属于我所敬仰的人物,我希望也能和他一样;我的傲气使我彷徨歧途,随风飘荡,但冥冥之中,我仍受你的掌握。
我真不知道,也不能肯定地向你承认我对他的敬仰,是由于人们对他的推重,还是由于他本人所具有的、 受到推重的优长?
如果那些人介绍同样的事迹,不赞扬他而带着指斥轻蔑的口吻批评他,我对他便不会如此热烈尊崇;事实并没有改变,改变的不过是介绍者的态度。
看,一个灵魂不凭借坚定的真理,便会这样奄奄一息地躺着,随议论者胸中所吐出的气息而俯仰反复,光明就被蒙蔽起来,分辨不出真理了。
其实真理就在我们面前。当时为我最重要的是说法使这位大人物看到我的言论和著作。
如果得到他的赞许,那么我更是兴致勃勃;如果他不赞成,那末我这颗习于浮华、得不到你的支撑的心将受到打击。
但我自己却很得意地欣赏着我献给他的那部《论美与适宜》 的著作,即使没有人赞赏,我也感觉自豪。
十五
我还没有看出这个大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妙化之中,惟有你全能天主才能创造出千奇万妙。
我的思想巡视了物质的形相,给美与适宜下了这样的定义:美是事物本身使人喜爱,而适宜是此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和谐,我从物质世界中举出例子来证明我的区分。
我进而研究精神的性质,由于我对精神抱着错误的成见, 不可能看出精神的真面目。
真理的光芒冲击我的眼睛,可是我使我跃跃欲试的思想从无形的事物转向线条、颜色、大小;既然在思想中看不到这种种,我便认为我不能看见我的精神。
另一面,在德行中我爱内心的和平,在罪恶中我憎恨内心的混乱,我注意到前者具有纯一性而后者存在分裂,因此我以为理性、真理和至善的本体即在乎纯一性。
同时糊涂的我认为至恶的本体存在于无灵之物的分裂中, 恶不仅是实体,而且具有生命,但并不来自你万有之源。
前者、我名之为“莫那特斯”,作为一种无性别的精神体;后者我名之为“第 亚特斯”,如罪恶中的愤怒,放浪中的情欲等,我真不知道在说什么。
原因是我当 时并不懂得,也没有人告诉我,恶并非实体,我们的理智也不是不变的至善。
犹如愤怒来自内心的冲动,内心动作失常,毫无忌惮地倒行逆施,便犯罪作恶;情欲起源于内心的情感,情感如毫无节制,便陷于邪僻;同样如果理性败坏, 则诐辞邪说沾污我们的生命。
当时我的理性即是如此。我并不知道我的理性应受另一种光明的照耀,然后能享受真理,因为理性并非真理的本体。
“主啊,是你燃 点我的心灯;我的天主啊,你照明我的黑暗”;[22]“你的满盈沾匄了我们”。
[23] 因为“你是真光,照耀着进入这世界的每一人”,[24]“在你身上,没有变化,永无晦蚀”。
[25]我企图接近你,而你拒绝我,要我尝着死亡的滋味,因为你拒绝骄傲的人。
我疯狂至极,竟敢称我的本体即是你的本体,再有什么比这种论调更骄傲呢?我明知自己是变化无常的,我羡慕明智,希望上进,但我宁愿想像你也是变易不定 , 不愿承认我不同于你。
为此,你拒绝我,你拒绝我的顽强狂悖。
我想像一些物质的形象,我身为血肉,却责怪血肉;我如一去不返的风,我尚未归向你,我踽踽而行,投奔至既非你又非我、也不属于物质世界的幻象,这些幻象并非你真理为我创造的,而是我的浮夸凝滞于物质而虚构的。
我责问你的弱小的信徒们——他们本是我的同胞,我不自知的流亡在外,和他们隔离——我纠缠不清地责问他们: “为何天主所造的灵魂会有错误?”
但我不愿别人反问我:“为何天主会有错误?”我宁愿坚持你的不变的本体必然错误,却不愿承认我的变易不定的本性自愿走入歧途,担受错误的惩罚。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六七岁,当时满脑子是物质的幻象。这些幻象在我心灵耳边噪聒着。
但甜蜜的真理啊,在我探究美与适宜时,我也侧看我心灵之耳聆听你内在的乐曲,我愿“肃立着静听你”,“希望所到新郎的声音而喜乐”, [26]但我做不到,因为我的错误叫喊着把我拖到身外,我的骄傲重重压在我身上把我推入深渊。
你“不使我听到欢乐愉快的声音,我的骸骨不能欢跃”,因为尚未 “压碎”。[27]
十六
我大约二十岁时,手头拿到亚里士多德的《十范诗论》,我读后即能领会,但这种聪明为我有什么用处?
我的老师,迦太基的雄辩术教授,提到范畴,便动容赞叹,当时的所谓博士先生们也都交口称道,我也想望羡慕,看作一种不知如何伟大而神圣的著作。
有些人自称非但听到明师的口头讲解,而且还得见老师们在灰沙中描摹刻划,才勉强领会;我和他们谈起来,除了我自学心得之外,他们也谈不出什么。
我以为这本书中相当清楚地谈到“实体”,如人,以及属于实体的一切,如人的外貌如何,身长几尺,是谁的弟兄或亲属,住在哪里,生在哪一年,立着或坐着,穿鞋的或武装,在做什么,或忍受什么,总之都属于其余九范畴,上面我仅仅举一些例子,即使在实体一类,便有无数例子。
这一切为我有什么用处?没有,反而害了我;我以为这十项范畴包括一切存在,我企图这样来理解你天主的神妙的纯一不变性,好像你也附属于你的伟大与你的美好,以为这两种属性在你身上好像在一个主体上,在一个物质上,其实你的本体即是你的伟大与美好,而其他物体却不因为是物体即是伟大美好,因为如果比较小一些,比较差一些,也依旧是物体。
因此我对你的种种看法,都是错误, 并非真理,都是我可怜的幻想,而不是对于你的幸福的正确概念,你曾命令过: “地要生出荆棘蒺藜”[28]我们原靠劳动才能得食,这命令在我身上执行了。
当时像我这样一个听命于各种私欲的坏奴才,能阅读一切所谓自由艺术的著作,能无师自通,有什么用处?
我读得津津有味,但并不能辨别出书中所有正确的论点来自何处。
我背着光明,却面向着受光明照耀的东西,我的眼睛看见受光照的东西,自身却受不到光明的照耀。
我不靠别人的讲解,不费多少劲,能理解一切有关修词、论辩、几何、音乐、数学的论著,主、我的天主,你都清楚,因为我的聪明,我思想的敏锐,都是你的恩赐;但我并不以此为牺牲而祭献你。
所以这些天赋不仅没有用,反而害了我。
我争取到我的产权中最好的一部分,我不想在你身边保守我的力量,反而往远方去,挥霍于荒淫情欲之中。
良好的赋禀, 不好好使用,为我有什么用处?
因为一般勤学聪敏的人认为极难理解的那些问题, 为我毫无困难,只有向他们解释时,才能感觉到疑难之处,他们中间最聪明的, 也不过是最先能领会我的解释的人。但这为我有什么用处?
当时我认为你,主、天主和真理,不过是一个浩浩无垠的光明物体,而我即发这物体的一分子。
唉,真是荒谬绝伦!但我当时确是如此;既然我当时恬不知耻地公开对别人传授我的谬说,向你狂吠,现在我也不顾愧赧而向你天主忏悔,缕述你对我的慈爱,向你呼吁。
当时我一无师承读通了难解的著作,但对于有关信仰的道理,却犯了丑恶不堪、亵渎神圣的错误,那么我的聪明为我有什么用处?
相反,你的孩子们,始终依恋在你膝下,在你教会的巢中,有纯正的信仰作为饮食,安稳地筹待羽毛丰满,长出爱德的双翅,即使思想拙钝,能有多大害处呢?
主、我的天主,我们希望常在你的羽翼之下,请你保护我们,扶持我们;你将怀抱我们,我们从孩提到白发将受你的怀抱,因为我们的力量和你在一起时才是力量,如果靠我们自身,便只是脆弱。
我们的福利,在你身边,才能保持不失; 一离开你,便走入歧途。
主啊,从今起,我们要回到你身边,为了不再失足,我们的福利在你身边是不会缺乏的,因为你即是我们的福利。
我们不必担心过去离开你,现在回来时找不到归宿,因为我们流亡在外时,我们的安宅并不坍毁,你的永恒即是我们的安宅!
注释
[1] 按指摩尼教徒。 [2] 见《诗篇》72 首27 节。 [3] 见《旧约·何西阿书》12 章1 节。 [4] 见《诗篇》40 首5 节。 [5] 见《约翰福音》5 章14 节。 [6] 见《马太福音》16 章27 节;《诗篇》50 首19 节。 [7] 按即卷七、第六章所说的文提齐亚努斯,是当时的名医。[8]见《新约·彼得前书》5 章5 节。 [9]纪元前第五世纪的希腊名医。[10]见《新约·罗马书》5 章5 节。 [11] 罗马诗人荷拉提乌斯(公元前65—8)的诗句,见所著《诗歌集》卷一,第3 首第8 句。 [12] 按这是公元376 年的事。奥氏在所著《驳学园派》一书中,对此次出游补充了一些细节。 [13] 见《诗篇》118 首140 节;《约翰福音》14 章16 节。 [14] 见《诗篇》79 首4 节。 [15] 译者按“道”即天主第二位,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 章,拉丁文为“Ver-bum”,或译为“圣言”。 [16] 见《旧约·以赛亚书》46 章8 节。 [17] 按指上文的“道”。[18]见《诗篇》18 首6 节。 [19]见《约翰福音》1 章10 节。[20]见《诗篇》40 首3 节。[21]同上,72 首9 节。 [22]见《诗篇》17 首29 节。[23]见《约翰福音》1 章16 节。[24]同上,9 节。 见《雅各书》1 章17 节。[26]见《约翰福音》3 章29 节。[27]见《诗篇》50 首10 节。[28]见《创世纪》3 章18 节。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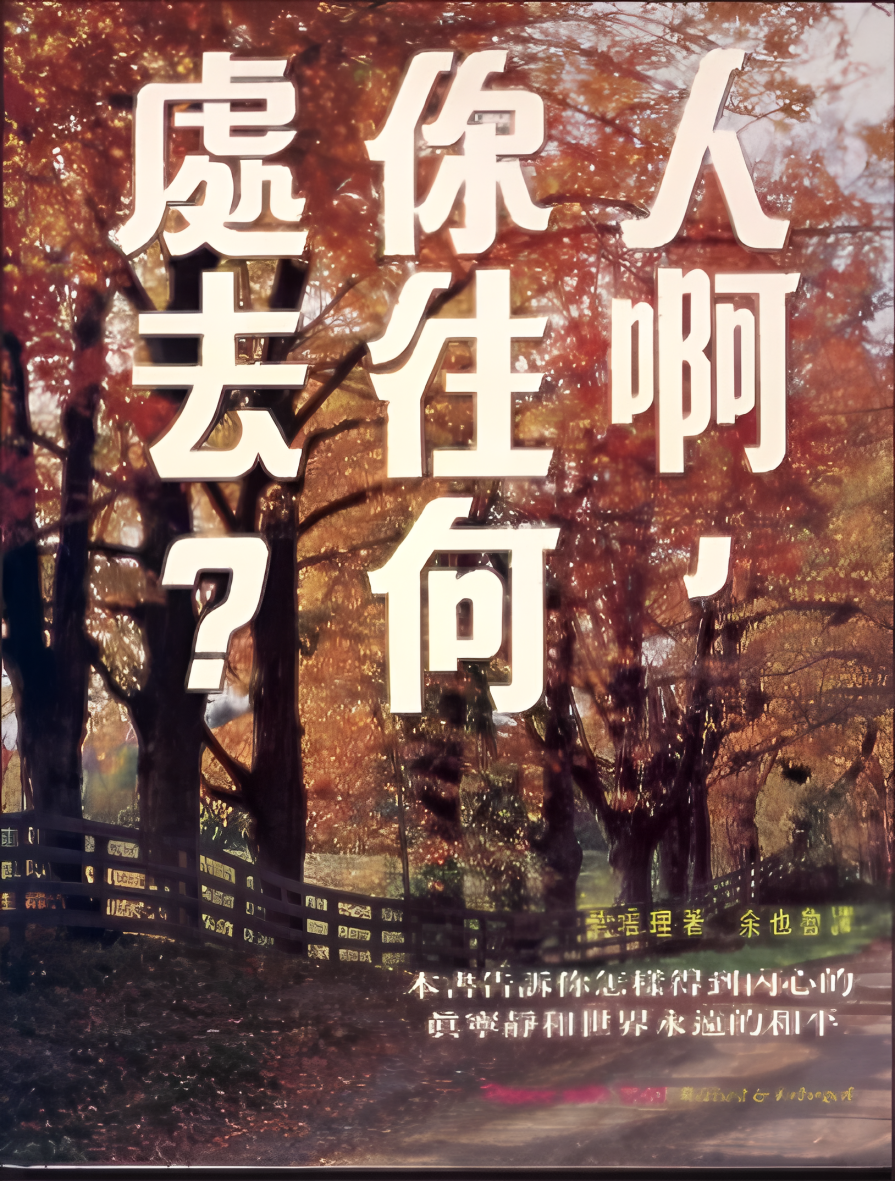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