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 第十二集 第三章: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归正

亲爱的听友您好, 我是主播宣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香港灵石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来》。
†
五十年来 第十二集 第三章: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归正
大有庄真是一个好地方。站在庄外就可以看见西山,出了庄口向南走不远,就是松树畦,那里有几百株松柏树,还有一道长的土冈,往西一直通到青龙桥街,冈上也长着不少松柏树。
走过青龙桥街便是青龙桥了。桥的下边是一道河,从南往北流过去,河水清得可以见底。
顺着河往上走,便是颐和园的后门。过了青龙桥往西南走,便是静明园,园里便是西郊胜境之一的玉泉山了。
从青龙桥街往北走,便可上到一座小山上面,山上有一块长圆的巨石,形似一只卧虎,所以那座小山名叫卧虎山。
(另一个说法是说,那座山的形状好似卧虎,未知二说孰是。)出大有庄向东南走,经过一条极清澈的小溪,再向正南,便是颐和园的正门。
我到大有庄的日子已经将近春分,正是草木萌芽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每日清早起来,便拿一本圣经走到卧虎山上跪在巨石旁边祷告,以后就坐在巨石上读圣经。
日间就走到河边,坐在石头上读圣经;读得疲倦了,就欣赏河内游泳的小鱼。
日落的时候,就坐在河边眺望远山的晚景。也有时走到附近的莹(营)地内,去读经默想。
天气好的时候就上到较高的红山顶上去唱诗祈祷。有时遇见乡人就同他们讲福音。
我那时读经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方法是把一卷书从头至尾细读一遍;另一个方法是查考一些重要的题目。
从3月16日到大有庄,至6月21日返城内,其间回家六次。实际住在乡间共有62天,那62天如同入了一次短期圣经学校。在真理上总算有了相当的进益。
5月28日曾得老友陈子诰先生自沧县来信,大意说,他听人传说我患了精神病,他对这种传说半信半疑,要我给他回信,详细报告一下我的近况。
我因为素日敬重他的信心、见识和人品,又因为手中还有十几圆钱的积蓄,便有意到沧县去同他谈谈。
因此就在6月27日离北京,经天津往沧县。次日同他作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他对我说,他确实知道我不但没有患精神病,而且是蒙了神的大恩。7月3日他嘱我在沧县城内礼拜堂讲一次道。
那是我蒙召以后第一次在礼拜堂中讲道。那天的讲题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7月5日离沧县回到北京。
七日的旅行,使我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得安慰,是因为我几年来敬重的良友承认我的确是蒙了神的特恩;得勉励,是因为在沧县的那一次讲道实在感觉到神的同在、满有能力和权柄。
这次的经验使我对神的选召和使命更加确信不疑了。
†
9月19日得陈子诰先生来信,大意说,夏天我那次在沧县讲一次道,很多人受了感动,现在沧县的中西同工都愿意邀我到沧县再作几天工。
23日又来了一封信,仍是催我前去。我在祷告以后,接受了他的邀请,便在9月30日离京赴沧,先后在沧县、盐山县、和献县的乡间,作工三个多月。
到了1月下旬,因为信仰,与教会的西国领袖发生冲突,便在1922年1月26日离开沧县,回到北京家中。
这三个多月作工的经验使我知道神不但选召了我,而且赐给我恩赐和能力为祂作工。
当时我揣想祂不久一定要交给我许多工作。不料神却把我关在家中,除了家中的琐事以外,什么事工都不给我作。这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我不明白神为什么选召了我却不使用我,我尤其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最令我难堪的环境中。
我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不能供养母亲,还要在家中吃母亲的饭,这实在是我不应当作、而且不忍作的事。
我尽力想减轻母亲的担负,但我没有路可走。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藉着得奖金供给自己入学的费用。
当我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伦敦会资助我读书。当我教书的时候,我可以藉着收入的薪金维持自己的生活。
姐姐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可以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家中十来间房子出租所得的十几圆租金,就归母亲自己使用。
母亲不但不要我们的钱,而且还拿她收入的房租给我们用。我们也尽力为母亲买些吃的东西或用的东西。
我们母子三人都过着独立的生活,同时也都彼此相顾相爱。可是这时我却成了母亲和姐姐的重担。
自然母亲和姐姐甘心给我饭吃,不过我却不能这样忍心长久累着她们。
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只有在家中作各样劳苦的工作,服事母亲和姐姐,减轻她们一部分担子。
因此我每天早晨起来洒扫院子和屋子,到街上去买菜回来烧饭,吃完饭,刷锅碗,洗衣服,补袜子。
母亲看见我作这些事,心中实在不忍,便催我赶快去寻觅职业,增加家中的收入,好雇一个女仆来作这些家务。
有时我软弱下来,想找一点事作,却找不着。有时别人来给我介绍职业,我又坚决不肯去就,只等候去作传道的工作。
作这些家中的琐事日子一久,心中便不免烦躁起来。我怪罪神为什么这样待我。
我似乎对神说,「从前我定志作政治家的时候,你一定召我去传道。
如今我接受了你的呼召愿意去传道,你又使我整日作这些劳苦卑微的琐事。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难为我?」我向神讲理。
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有时我苦痛得不愿意活下去。也有时我一面操作,一面生气,甚至把东西摔在地上。
有一天我读出埃及记,看到摩西被神带领到米甸旷野、牧羊四十年的事迹,我忽然明白过来,知道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功课是从苦难卑微的事工里学出来的。
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便死心塌地、殷勤忠心的去作这一切家中的琐事。
扫地、擦桌、烧饭、刷碗、洗衣服、补袜子,我都尽心竭力的去作,而且要作得尽美尽善。
我那时明白作这些琐事与传神的道是同样的重要,也有同样的价值。又知道如果这些琐事作不好,将来传道的工作也一定作不好。
到了最后我竟学习到一种地步,认为如果神使我一生就作这种卑微的琐事,我也从心里说「阿们」。
†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
及至我在家中作了三四年劳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作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神,到了这个程度,祂才开始把祂的工作交给我。
1922年1月26日由沧县回到北京以后,那一年就一直困处在家中那间小棚子里,每日除了作这些家庭中的琐事以外,便抽些时间研读圣经。
1923年的前半年仍是这样。1923年7月31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到元氏县,下车转往我的一个学生的故里赞皇县城的内地会主领八天的聚会。
14日会毕,经过元氏、正定两县,往行唐县,预备到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石天民家中去,不料19日到了行唐县城内就开始患病。
休养了几天,越来越重,便在25日带病返京。到京以后病更转重,直到9月下旬才痊愈。以后仍继续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一直到年终。
1924年3月4日经人介绍,被邀偕同本城各教会约三十多位中西传道人赴南苑军队中布道六天。
那是我第一次与各教会的中西传道人共处。所见所闻的事,实在令人疾首痛心。
虽然那些传道人中也有很少数的几位给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可是大多数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基督的仆人。
六天布道的结果,据说有二十多人受洗。我从各方面观察,发现那些报名受洗的人中间,真诚悔改信主的实在是少得可怜。
当他们大家热烈筹备要在11日举行施洗盛典的那一天清晨,我因为不忍目睹那一种可哭的情形,便乘进城的大汽车返城了。
那几天工作的经过,使我更认识了中国教会的腐败、虚空、贫穷、可怜,也更激发了我为神作工的热诚。
6月3日离北京外出工作,先后在天津西董家庄、沧县、萧张镇等处讲道。
7月2日离了萧张,经过德县往济南去,看望一位通信数月、彼此渴望见面的弟兄,在他那里住了十二天,双方都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
7月15日由济南到天津工作数日。24日又赴沧县小住六天,31日回到北京。
8月30日离北京赴德县,在公理会与伦敦会合开的教会领袖聚会中讲道。
听见一个不信基督的传道人大讲混乱圣经真道、败坏听众信心的言论,心中激愤不安,经过长时间恳切的祷告以后,放胆在聚会中把他所讲的一切错误都一一指正出来,因此惹了那些与他同类的人的怒气,以致他们向我大肆辱骂和攻击。
这是我公开与教会中的恶势力宣战的第一次。感谢神,祂率领我在基督里得了胜利。9月2日再到沧县工作十几天,18日回到北京。
†
这次从外面回来以后,仍然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正在这时候,家中外院住的一家邻舍迁走,空出两间房子来,我因为这时自己有一点收入,可以补助家中一些用度,便同母亲商议,把这两间房子让给我用。
因为那些时候常有人到我这里来谈道查经,我本来住的一间棚子太狭少,不敷应用。
母亲答应了我,便在10月4日从一间小棚子里迁到两间屋子里。
从前在小棚子里住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常到我这里来查经,后来又有一位少年人参加。
到这时候房子的容量加大,可以容纳较多的人,10月18日开始在新房子里聚会,便有三个人参加。
25日的聚会有五个人参加,以后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到的人有时更多,有时较少。
从12月24日起,又增加每星期三的查经会,第一次三个人参加,第二次六个人到会。我在北京传道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24年中也开始写几种小册子印刷分赠。那一年中出版约有四种:计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恶世中的呼声」、「基督徒与偶像」、「基督的十字架」都是六十四开本的。
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1925年的春季,工作大大展开,这些事我要留在下一章里述说。
这里我要述说一些1921至1924年间我在信仰上的转变。
当我从保定被逐回到北京以后就到为我施浸的朱先生所在的那个聚会去。
那个教会以前叫「信心会」,那时已经改名为「神的教会」。
那里的领袖是一位挪威国的老人,是作工程的。那里聚会的人数,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位。
他们没有礼拜堂,只是在那位老人的会客室中聚会。
那位老人不会讲什么,每次聚会总是说,「我们要遵守祂的诫命,不离开罪不能见主,人不圣洁不能得救。」
这位老年人像其他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一样的主张不说方言便是没有受圣灵。
他也主张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他却接受新西兰一个信徒所讲的,说在亚洲的第一日实在是第七日,因此在亚洲各国家中的信徒应当以星期日为第七日的安息日,欧美各国的安息日却是星期六。
他不信人一经悔改信主便可得救,他认为世上没有那样容易的事。
他主张一个人信主以后必须追求圣洁,直到他完全离开了罪,才可以得救。
他教训人离罪的方法更可笑了。他把新约里所记的种种罪恶列出一张表来,一共八十三样,把这张表挂在屋子里,教人每天念这些罪恶的名字。
他说,这样做慢慢就能离开它们,成为圣洁。此外他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他却讲不明白。
跟随他的那一小群信徒差不多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有的人只能念圣经,有的人连字也不认识。
我才一到他那里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新鲜的,倒也有一度对他们很倾心,但日子一久,我这颗饥渴的心便感觉不能满足了。
讲不圣洁不能得救的人所有的人生并不圣洁,那些说方言的人所说的方言渐渐也使我发生了怀疑。
守安息日的事也不过是讲讲而已,实际就没有几个人真能彻底的去守。至于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更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
我虽然对这个老人和他所讲的道理不能满意,有一点,我却与他的见解相同,就是那种「不圣洁不能得救的道理」在我认为是十分合理的。
†
我从十四岁信主以后,便有一种强烈恨恶罪恶、羡慕圣洁的心志。我每逢自己犯了罪以后,便痛悔自责;每逢看见别人犯罪,也疾首痛心。
我看见教会中充满了各样罪恶,就义愤填胸。我不信这些终日活在罪恶中的信徒们能得救。
我恨罪,因此我断定,不离开罪、不成为圣洁的人绝不能得救。
我既有这种信仰,心中便常不得平安,因为我发觉我还没有完全离开罪,我还不够圣洁,当然我不敢说自己准能得救。
我信主耶稣能赐给人永生,我盼望主来接信祂的人,但我自己究竟能否得救?我却没有把握。
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信徒说他已经得了救,我一定斥责他为大胆狂妄。我既没有得救的把握,当然常常战兢恐惧,恐怕一生信主结果仍是被主弃绝。
我那时候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是在西奈山下面战栗徘徊。
那位挪威老年人所住的院子里还住着一位瑞典国的老年人,名叫毕胜道。
他常常讲因信得救的真理。他和那位挪威老人所讲的道完全是相反的。
他住一间小屋,穿着很不整齐的衣服,吃很苦的中国饭。
他是一个很贫穷的外国人,而且常患着病。我因为看他年老无依,常去看望他,希望给他一点安慰,他就顺便对我讲一些因信得救的真理。
我起初不能接受,但他所引证的一些经文渐渐在我心中作起工来。
到1923年的春季,我的思想开始改变。那年2月27日在日记中写了一篇祷告文说:
「在天之恩父钦,仆今深知世人于尔前无一义者,更无一事可以自夸。本诸罪罚皆当死亡。惟尔施恩宏溥,遣尔于耶稣代赎人罪,使凡信之者皆得白白称义。仆今后不复追求赖行称义,惟愿完全接纳吾主耶稣之宝血,赖吾主为仆之救赎者。仆又愿以被赎之身心完全奉献于父前。仆既为重价所赎者,则此后之生皆不复为己而生,乃愿完全为父及吾主耶稣而生。今祈父赐特恩,赐圣灵充满仆衷,使仆今后完全接纳吾主耶稣于仆内行作万事,一生所夸惟吾主之十架。更祈尽去仆之骄傲错误,使仆毕生行于光中。愿父旨成于仆身,父名在仆得荣。皆奉吾主耶稣之名。阿们。」(1923年2月27日日记。)
†
对因信称义的真理彻底明了的那一天,日记中有以下的记载:
「我罪污如何洗去?惟有耶稣所流宝血。我心病如何能愈?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奇哉恩波浩荡!此外活泉无望。我心得洗雪亮,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心得洁并非在己,惟有耶稣所流宝血。罪得赦别无可倚,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我无法可掩疵玷,惟有耶稣所流宝血。我无德可以上献,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哪是我盼望平安?惟有耶稣所流宝血。得称义蒙主喜欢,惟因耶稣所流宝血。
「暮于室中歌耶稣宝血一诗,心甚有感。歌之数遍,又歌耶稣受死之诗数首。十架之工斯际于予心乃十分清淅。顿觉千钧重担乃于十字架前完全脱落。快愉莫名,高声祈祷,颂美神恩。」(1923年3月9日日记。)
完全明了这因信称义的真理以后,在信仰上可说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幸而神在以前没有为我大开工作的门,否则把道理讲错了,可怎么收回呢?
从那时以后,我便不再多与那位讲律法的老人来往,同那位帮助我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老人来往却渐渐多了起来。
那年六月间他介绍一些英文的阐道小册子给我,嘱我译成华文,并代那些出版小册子的圣徒们每月转给我十几圆钱的馈赠。我帮忙这种工作有二十三个月之久。
直到1925年4月底才放下。毕君也在那年11月间因病去世。
我因为守安息日的缘故,听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是守安息日的,便引他们为同志,在1922年的春夏二季中到那里去聚过几次会。
可是去了几次以后,所得着的不过是失望,因为他们除了几样特殊的讲法以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满足我心灵中的需要,因此以后也就不去了。
我从1921年直到1926年都主张守安息日。但后来我发现使徒在书信中竟没有一次教训外邦的教会守安息日,我开始对这种主张发生疑问。
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祈祷与查经,我明白了神并未曾吩咐外邦的圣徒必须守安息日,至于称第一日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更是人的遗传。
关于安息日的问题,我曾印了一本小书,名字是「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吗?」在这里我就不再多叙了。
关于说方言的事,当我受浸以后约有一年多之久,我接受五旬节派的道理,并且也那样传讲,就是说,「一个信徒受圣灵必须说方言,因为说方言是受圣灵惟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信徒就未曾受圣灵。」
有些人作见证说,在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怎样得着极大的力量,怎样自己约束不了他们自己的舌头,好像有一种能力支配着他们的舌头,因此说出他们自己所不明白的言语来。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我发过一些自己所不明白的声音,原因还是由于上文所说不住的喊叫「哈利路亚」那种祷告。
到今日我认为那是一种机械式的方言。起初我还没有什么疑问,到后来看见听见许多人说那一类的方言,渐渐引起我的疑问。
有些人说方言的时候只有一两个单纯的音调,就如有人只说「吧、吧、吧、吧」;有人只说「搭、搭、搭、搭」;有人只说「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总是这个声音。
请问这如何能叫方言呢?就是天使说话也不能用一两个音表达许多意思啊!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自己祷告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方言,他们在那些不注重方言的聚会里也从来不能说方言,只有到了注重方言的聚会里才能说方言呢?
更有一件使我感觉奇怪的事,就是许多人的行为、生活非常不好,可是他们祷告的时候仍然说方言。
1921和1922两年间,我看见一个青年人,他的性情凶暴残忍像一头野兽。
他虐待他的母亲和妻子的情形令人看了皆裂发指。他还有种种的恶行,使人无法承认他是基督徒。
可是他一跪下就能说方言,而且他所说的还不只是几个单纯的音,他所说的真像一种语言一样。
†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又看见许多真诚信主、热心事奉神的圣徒,其中有的人生活敬虔,满有主耶稣的香气,也有的人为主作工大有能力和权柄,但他们却未曾说过方言,难道他们没有圣灵吗?
我再查考圣经,便发现每一个基督徒在真心悔改信主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
有神的应许为这事作见证,比人所不明白的那种声音更为可靠。
因着这一切的真理和事实,使我放弃了我在受浸以后所接受的那种教训。
我在那几年留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完全把我从前在教会里所听见过的道理抛开,只是查考圣经。
凡是圣经里所有的,我都接受;凡是在圣经里面不能找出来的,我都抛弃不顾。
凡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我没有一样不信,同时我也不愿意信一样圣经里所没有的道理。
我不曾读过圣经注释。我最不欣赏那种书籍。我今日讲道和治理教会都以圣经为惟一的准则。
我不愿意接受一点教会的遗传和人所制定的规则,我更不能与任何背道犯罪的事妥协,我也绝不对抵挡神的人让步。
我因此离开了我从前所隶属的教会,我也与上文所说的那个教会断绝了关系。
我在那时还不知道神怎样用我为祂作工,更一点没有意思要起始一个新的工作。
不料神竟一步一步的引领我走到今日这个地步。
祂的作为真是奇妙!连我自己回想起来,也不能不感觉惊奇呢!
追述一下二十多年以前的经历,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在那个时候却是饱尝了无限的辛酸,吃尽了诸般的苦味。
有些时候真觉得度日如年,有些时候苦得甚至想要求死。逼迫、反对、笑骂、侮辱、误会、伤心,种种的滋味都一一的尝了再尝。
谁想到那一切都成了今日的益处呢?以前我只是念诗篇上的话,现今我经验过了这些话: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六十六10-12)
1948年12月3日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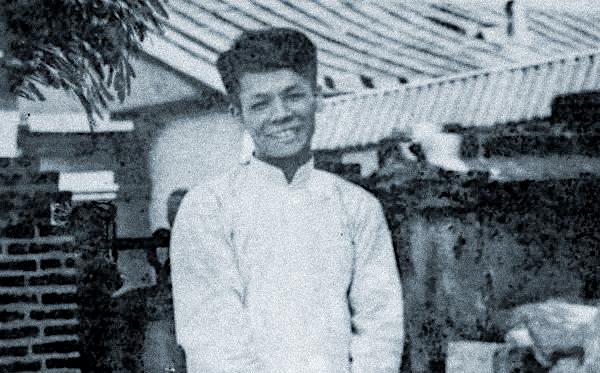
发表评论